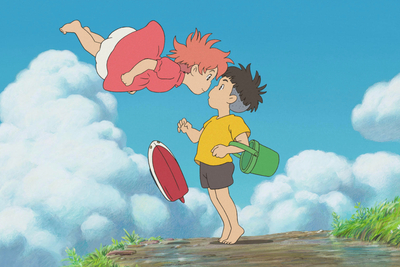文:楊世賢、薛守岑、石守玉、陳羿妏、黃立婷、吳菊芬
圖片提供: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講者:張素卿(Kiki)、魏世雅
目前就讀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的Kiki,回想起入學考試時的情景,當時她被問起:「兒童文學的三大隱憂為何?」Kiki回答的其中一項,便是「兒童音樂的消失」。也許並無所謂的偶然,但Kiki心中對兒童文學的關懷,帶領她遇見與兒童音樂合作的機會。
娃娃兵進音樂廳的挑戰
2011年,四也文化初成立,隔年Kiki至北京時在因緣際會下認識了當時臺北市民交響樂團團長高錦弘,也讓 Kiki 知道有「娃娃兵進音樂廳」這樣的活動,臺北市民交響樂團將經典故事與音樂結合,為孩子舉行音樂會,那一年已是第十三年演出了。由於四也文化出品的書籍大多來自本土創作者,高錦弘也因此向Kiki提出了合作邀請,進一步促成娃娃兵進音樂廳的第十四場演出。
2013年的「娃娃兵進音樂廳」,是四也文化與市民交響樂團的首次合作,Kiki分享了選材上所遇到的困難——當時四也文化的出版系列僅兩套,分別為《童話搜神記》和《福爾摩沙冒險小說》,可以選擇的文本並不多,而最後決議以《媽祖的眼淚》呈現。不過《媽祖的眼淚》對市民交響樂團的許多團員而言有宗教方面的疑慮,但在高錦弘的積極說服下,團員才接受這次演出是傳達「非宗教而是文化」的旨意。
除了媽祖之外,接下來的兩年則以土地公和門神的故事為主題進行演出。到了2016年,四也文化和市民交響樂團開始嘗試不同風格的演出,除了儘量避開帶有宗教色彩的主題,表演場地不再侷限於臺北國家音樂廳,當年度的演出《快樂點心人》一共演出三場,分別在臺北、新竹和彰化舉行。
四也文化與市民交響樂團也經歷了許多表演者都會遇到的場地問題。《快樂點心人》的演出本來是由彰化縣教育處聯絡各國小的小學生觀賞表演,然而在演出前一天,團隊才知道受邀參加的只有某間國小的兩個班級,僅有約五十人,但表演廳本身能容納四百人,人數落差非常大。因此,Kiki和市民交響樂團執行長緊急四處打電話聯絡所有能幫得上忙的朋友,最後在三個小時內成功邀請了五百多位居住在演出場地附近的孩子前來欣賞演出。
娃娃兵進音樂廳的演出之路遇上了種種挑戰,直到2019年的作品《我的獵人爺爺》才為四也文化帶來重大改變——漸漸擁有「話語權」。當時演出雖然售票狀況不佳,但內容涵蓋的原住民文化也使得不同族群找到四也,希望能透過合作,一起將獨特的文化保留下來。
《動物園大搬家》源起
回憶2020年的演出《動物園大搬家》的緣起,當時繪本創作者李如青帶了以大象「林旺」的一生為主題的影片《最後的戰象》到四也文化提案,決定以此為題材後,四也文化也和李如青一同梳理林旺的生命歷史:自1917年在緬甸出生,到二戰時被俘虜,一直到牠最後到了臺灣生活,最終進入木柵動物園。
這部作品後來以三部曲的方式陳述,希望能更完整地呈現林旺的一生,另外,在創作過程中也花費很多時間發想不同的意象,最終以叢林、海洋和城市進行不同的封面設計。李如青和四也文化一直想將故事搬上舞臺,卻沒料想那一天卻會這麼緊湊的到來。由於表演時間提前,繪本卻尚未出版,但為了將故事搬上舞檯,他們決定在取得故事版權後,與市民交響樂團通過戲劇的方式呈現。《動物園大搬家》搬上舞臺的過程雖然波折,但仍可看見雙方想將作品做到最好再呈現給觀眾的用心。
《動物園大搬家》登場:細節傳達意念
《動物園大搬家》登上大舞臺,對團隊而言的第一個考量是「話語權」,也就是作家欲傳達給觀眾的意義,例如《我的獵人爺爺》傳達出布農族獵人與黑熊的關係,而林旺爺爺的一生如老兵般顛沛流離,最後來到臺灣安身立命,這個故事想表達的其實是「反戰」。不過,娃娃兵進音樂廳的觀眾多數為兒童,整個團隊便要以此年齡層的觀點發想,最後以「家」的概念發想,轉換成兒童可理解的方式呈現。
為了讓《動物園大搬家》能精準傳達作家與團隊想傳達的想法,從繪本、劇本、臺詞、刊物、宣傳海報至舞臺設計都做了許多調整,例如道具輸出後發現道具與舞臺比例不合,只好在表演前緊急重做,即便當時正值過年期間,團隊為了呈現最好的一面,仍然不分日夜加緊趕工,一直到表演彩排的前一刻都仍在修正,最後才讓《動物園大搬家》順利登場。
四也文化與市民交響樂的演出是相當成功的跨界合作案例,繪本、音樂、美術、品牌行銷、戲劇監製、劇本撰寫團隊裡人人各執所長,才使得《動物園大搬家》能順利搬上大舞臺。Kiki強調,想進行跨界合作,首先還是要對該場域有深入理解,才能開始接下來的合作洽談。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多和不同生活圈的朋友多相處多接觸,對自己在未來無論哪一面向的合作或許都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幫助。
音樂:流動的建築
娃娃兵進音樂廳的活動萌芽,源自於音樂廳的限制:六歲以下的兒童無法進入音樂廳,而市民交響樂團是由眾多愛樂者組成的團體,大家其實很希望藉由孩子進到音樂場域,聽到、看到、感受到整個音樂廳的氛圍,進而培養古典樂的興趣與品味。他們也就發想了「娃娃兵進音樂廳」的計畫,市民交響樂團音樂總監魏世雅說:「學文學的人喜歡用音樂說故事,學音樂的人則喜歡用文學說故事」。「音,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為什麼講「生於心」,說的是那個聲音是有概念、有意圖、有設計與邏輯的,而不是噪音。
「有人曾說,音樂是流動的建築,當音樂一出現的時候,會把我們的空間整個改變。」魏世雅指出,建築在我們的觀念裡是固定的,但是當音樂出現的時候,它能隨時讓你置身在另一個空間裡。娃娃兵進音樂廳的活動,便是希望透過音樂,從平面故事中引導出立體的空間與畫面,讓時間隨著音樂的流動進到幼兒想像力的世界。
原住民音樂 X 古典樂?
在《我的獵人爺爺:達駭黑熊》的演出中,樂團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原住民音樂和古典樂的結合,最後決定由大自然和布農族部落出發,選擇適合的音樂塑造中央山脈的沈穩、群山綿延的形象,接著參考角色形象、情感、故事寓意並與古典樂結合。
這些過程中最大的考驗還是布農族歌曲該用什麼方式呈現?在經過許多的討論與深思熟慮後,交響樂團決定以原音呈現布農族文化。魏世雅認為,原住民文化就用他們慣常的方式表現,而透過「尊重不同族群」的形式,可以讓我們學習不同文化,也能夠讓進入音樂廳的孩子帶走些什麼。
劇情中的音樂細節
魏世雅在為音樂劇選擇音樂時,角色特質和調性是考慮的條件,例如有一幕是林旺不願意搬家,因此管理員拜託馬蘭(林旺的太太)勸說。相較於兩拍這種適合用在進行曲的重音頻率,或是四拍這種較規矩的元素,三拍通常會使用在圓舞曲,也適合馬蘭這個比較柔性的女性角色。
動物們搬到木柵動物園後,劇本中有一段設計林旺以獨白表達對於新家的感動,此時搭配的音樂是以前被改編成中文歌曲的〈念故鄉〉,用這首歌讓林旺回想他生命中所有過程——從最早在緬甸,後來輾轉到高雄到圓山,最後落腳在木柵。這段音樂裡有個樂器叫英國管,是個充滿感情、溫暖音色的樂器,極其容易觸動聽眾對一些回憶的共鳴,而配合這個片段的演員更是用心,即便沒有演出時,也會不斷複習這段樂曲,再不斷背誦臺詞,讓自己講述臺詞的節奏能與音樂合而為一。可見一齣成功的音樂劇所需具備的條件太多了,無論幕前幕後皆需要專業人士各司其職,方能使其完整呈現在你我眼前。
對魏世雅來說,最大的挑戰是林旺兒時在緬甸的那段充滿戰爭元素的回憶,要選用哪段音樂表達戰爭的冷酷無情和潛藏背後的人物情緒呢?那就選擇蕭士塔高維奇(Shostakovich)的〈第五號〉吧!蕭士塔高維奇是俄國人,在史達林的共產政權統治下,蕭士塔高維奇並不能太醒目的反抗上位者,僅能在一些曲式、和聲等地方表達自己的抗議,這首歌代表的就是反抗、抗爭的音樂,正好符合林旺這段晦暗、迫於現實無奈的場景。
後來緬甸戰敗,大象歸中國軍所有,必須跟著修路、運送貨物等,此段的音樂都是採節奏緩慢、旋律和跳動性不那麼大的曲子,最後孫立人將軍把大象們送到臺灣,不管孫將軍或林旺對彼此都已經有不捨與依戀,因此魏世雅選擇利用長笛獨奏的一段音樂來描述這樣的情感:一個面臨必須離別、不得不分離的意涵,而最後音樂也刻意地停留在這,剩下的情感部份讓孩子去細細品嘗、慢慢回味。
當然在整個音樂劇裡不能一直都是沉悶的樂曲,因此魏世雅在設計編排的時候會考量高低起伏、緊湊有趣的音樂,像是從圓山動物園搬家到木柵動物園這段就安排〈庫斯克郵車進行曲〉(Csikós Post),讓觀眾感受到雀躍、高亢振奮的情緒。
音樂劇最後如何結尾呢?魏世雅強調音樂是一種共通的語言,用什麼樣的音樂代表什麼樣的情緒轉折,「音樂術語裡最後的結尾叫coda,是『尾聲』,意思就是說,其實曲子已經可以結束,話也講得差不多了,但好像就是想起了什麼,感覺就想再拉長一下。」她舉《屍速列車》最後一個片段當例子,導演利用樂曲〈珍重再見〉(Aloha Oe)作為最後一幕的coda,將「珍重再見」的意涵透過女主角輕哼,讓觀眾體會對於離別的無奈與努力生存的決心。
厲害的尾聲會讓觀眾回味無窮,如同前述所謂「聲於心」一樣,將作者的意念、想法、思考、語言,透過音樂做為溝通工具,觸及人心。
Q&A
Q:演出之前的整體工作流程如何規畫進行?
魏世雅從古典音樂切入說明,「娃娃兵進音樂廳」在前十三檔的模式,是先寫故事出來,再從故事裡去找合適搭配的古典音樂片段。開始和四也文化合作後,會把重點放在尋找適合的繪本,首先會以繪本對象適宜度當作首要考量,再來依照繪本調性與故事性進行整體音樂規劃,因為目的是將古典音樂呈現在孩子面前,讓孩子進到古典音樂的世界。
至於需不需要擔心孩子聽不聽得懂?魏世雅一直相信孩子就像海綿,透過故事與音樂的演出,會帶給孩子們更多的經驗與想像,這也增加他們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Kiki也指出, 因為這齣劇著重點在音樂,因此演員必須能在音樂掌握上有一定程度,特別是交響樂,也因為這樣,演員其實也是樂團團員擔綱。另外,在導演的部分都是外聘,在聘用時會根據不同條件安排,這使得「娃娃兵進音樂廳」一系列十幾年演下來,經過很多不同導演,就合作經驗來說增加了很多不同的養分。
Q:當天演出時,音樂與戲劇的音效是同步進行的,故聽不到音樂部分此點稍嫌可惜,這樣的音樂感受是傳統延續下來的嗎?若能多一個空間是能讓孩子感受細節嗎?
魏世雅回應,這個問題在設定音樂時很糾結,雖然設定上是一個音樂會,讓孩子能走進音樂廳欣賞演出,所以會希望能多點留白讓孩子單純體驗音樂會。但會因為故事劇情、臺詞與音樂重疊部分不同,進行些許比例刪減。若是情感上的抒發,會有較多的片段留白,多一點的音樂填補,單純的讓觀眾用「聽」的。
綜合以上,從故事素材的選取,音樂元素的注入,以及將兩者結合以戲劇方式呈現,如果說「娃娃兵進音樂廳」這樣的創作,意在使兒童進入古典音樂的世界,倒不如說透過不同領域的合作,為兒童呈現出另一種可以「閱讀音樂」的可能性,這樣的形式無疑是成功的。期待未來,不僅能在古典音樂的基調中,能夠看見更多與不同媒材的演出,也希望這樣的可能性,更能實際在教育裡發展出可執行的路徑,打破只能進劇場觀賞的侷限,變成人人都能隨手聆賞的可能。

圖說:市民交響樂團音樂總監魏世雅和兒文所所長王友輝合影。

圖說:四也文化出版公司總編輯Kiki和兒文所所長王友輝合影。
責任編輯:陳惠伶、羅雅詠、林岳鋅、李暉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