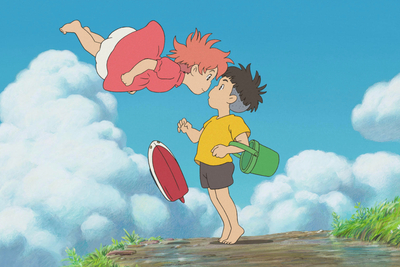文:薛巧妮
圖:取自網路
照片:感謝林佑儒老師提供
那天在某間咖啡館,林佑儒的行李箱沉靜地靠在角落,諦聽主人與編輯的談話;桌邊明淨的大窗隔絕了臺北午後的悶熱與瀑布般的陣雨,窗戶漸漸起了霧,街景宛若籠上一層薄紗,對談中的兩人不停穿梭於不同時空……
那一下午,林佑儒一下子是甫獲知名文學獎的新銳作家,一下子是出版數十部作品的資深創作者;她也一下子是在糖廠長大的書小孩,一下子是善解人意的國小英語教師,一下子又是賢淑知性的妻子與母親。然而,無論年紀、身分與心境怎樣轉變,林佑儒不變的始終是她那道獨立善思的靈魂,以及堅持寫作的毅力。
2003年,林佑儒33歲。那年,就讀兒文所的她,獲得人生中第一座文學獎──九歌少兒文學獎,後來出版處女座《圖書館精靈》,從此踏上漫漫作家路。如今,她的寫作資歷逾二十年,曾獲吳濁流文藝獎、南瀛文學獎等,並著有「神祕圖書館偵探」系列、《會飛的祕密》、「草莓心事」系列、「廁所幫少年偵探」系列等書。





無論是詼諧純真的校園生活、情竇初開的少年少女、鬥智鬥勇的偵探冒險、瑰麗細緻的奇幻想像,這些作品陪伴無數小讀者長大:畢業多年的學生回校找她敘舊,或牽著自己的孩子出席新書活動;亦有讀者長大成為編輯,面對面採訪她……他們無一例外地受這些故事召喚,不管時隔多少年,仍能循路回到各自的童年;文字是路標,是漢賽爾與葛麗特遺下的石子,不管時隔多少年,仍不會被雀鳥食盡。而林佑儒或讀或寫,「童年」都是一道伏流,流動於她的生命中。

童年閱讀是起點,童書少不了童心
林佑儒從小在花蓮的光復糖廠長大,而糖廠社區生活在她的記憶裡始終明媚鮮活,就像一幀幀毫不褪色的照片;鄉下生活即使一陳不變,依然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那兒有學校、活動中心、理髮廳、診所、網球場、早餐店、懷舊的日式澡堂,還有她最重要的據點──閱覽室。如果你的視線聚焦於其中幾幀照片,就會發現她的童年有許多時間在糖廠社區的閱覽室度過。
「我的童年經驗是很重要的靈感來源。」林佑儒說,無論是乘著安徒生、格林等經典童話而一頭栽入汪汪書海,或是受到《國語日報》與國立編譯館《中華兒童叢書》所啟蒙;抑或推開門扉,只是單純地跑跳遊走於東部的山水之間,靜靜仰望滿天星斗……她的童年萬幸未被課業壓力給淹沒,而是保有孩童自主探索的樂趣與自由。
作為孩童的心境,至今依然被林佑儒深深銘記。所以,她最早的創作即從「童話」這個適於兒童心理與興趣的文類開始。即使整個社會環境馬不停蹄地隨著時代變遷,她認為,童心是不會輕易改變的;所謂的「童心」,就是兒童面對這個世界,以及置身其中的人事物最原始的看法與反應,孩子們因什麼快樂,因什麼幸福,因什麼憤怒,因什麼恐懼,又因什麼悲傷……這樣的赤子之心,她一心一意期望能注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具體而言,林佑儒創作故事時,都往這只滾滾湯鍋拋入哪些材料呢?
首先,小讀者閱讀的樂趣不可或缺。要從小孩的視角出發,看一部故事怎樣是「有趣」的,哪怕這些事件在大人眼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很無厘頭,「比如說,我小時候在糖廠附近捉到一隻又大又美麗的鳳蝶,我想做成標本,卻不知道該怎麼做。我想起媽媽教我做過押花,做法是把花瓣夾進書頁裡,讓它自然乾燥,於是異想天開,也把鳳蝶夾進爸爸厚重的工程書中。那本書的下場──可想而知,最後生了很多螞蟻。我爸爸拿起那本書,他非常生氣,但我已經忘記有沒有挨罵了……」
說起孩提糗事,林佑儒忍不住笑了出來:「這件事情,很顯然的,是因為小孩子缺乏自然知識,嘗試中出了錯,但它卻是我非常寶貴的回憶。而且,小孩子最直覺、最原始的思考正像這樣。」在她看來,兒童的任何嘗試,結果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可貴的是這段歷程與經驗,這也是她的故事要素之一。
再來,「想像力」是畫龍點睛的調味料,讓故事的層次更豐富。林佑儒小時候閱讀簡易版的《愛麗絲夢遊奇境》,對這個故事著迷不已,「愛麗絲從現實出走,踏入另一個世界,過程中非凡的冒險,有趣得不得了。所以,我喜歡寫貼近生活的故事,其中又不乏奇幻的冒險;不全然虛構,卻也不全然寫實。」
不過,儘管曾為小孩,現在並非「兒童王國」一員的林佑儒,如何理解不同世代小讀者的感受和想法呢?她徐徐答道:「沒有錯,時代變了,現在小孩的生活跟我那時候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兒童純真的本質、他們普遍擁有的內心,讓作品足以跨越時空的限制。唯一不一樣的是,當代兒童的生活中充滿視覺與聲光刺激,大大降低了他們對外在事物的好奇心與觀察力,所以,我也時常藉由閒聊或故事,喚起他們對生活周遭的關注。」
貫徹作家精神:對寫作心心念念
每位作家的寫作習慣與堅持不盡相同,他們往往也有很不一樣的目標。林佑儒是如何看待自己這個身分的呢?
「剛出第一本書時,我不認為自己是『作家』,而是一個『作者』。後來我持續寫作,但依然不認為自己是個作家,那時我才剛從起點出發,那是邁向『作家』的起點。」對她而言,作家不光是「創作詩歌、文章或其他藝術品的人」而已,「作者」與「作家」在字典裡雖為近義詞,兩者之間卻存在關鍵差異──寫作持續力。她曾聽聞一位出版前輩說過:「只出過一、兩本書的人,他們並不算『作家』,起碼要有十部著作,才能稱為『作家』。」
林佑儒認為,寫作的「耐力」與「熱忱」是作家的潛在特質,它們雖不能保證文學夢個個成真,卻缺一不可。她本人便經歷過這般「捫心自問」的過程,「寫作多年後,我的作品已經累積了一定數量,在那樣的時刻,我發覺自己心中仍存繼續創作的意念,心中仍有想要挑戰寫出來的主題,我才賦予自己這樣的身分──我是一個兒童文學創作者,我是一位童書作家。」
在編輯眼中,林佑儒向來是個很自律的作家,幾乎不拖稿。沒想到,她對「自律」卻有不同理解:「除非有重大事情,我確實很少拖稿,在截稿日之前,死活都會把稿子寫完。不過,我往往利用週末或寒暑假寫作,平日零碎的時間反而不一定能善用;而且,我也很少寫故事大綱,通常是心中已有故事面貌,再一筆一劃慢慢描繪出來……說實話,我覺得自己還不夠『自律』。」近年來,她嘗試培養新的寫作習慣,更有紀律地寫作;先擬好故事大綱,每天不間斷地至少寫五百字。剛開始很不容易,堅持了一段時日後,她漸漸嘗到「紀律」的甜頭,越寫越順暢。
此外,林佑儒在長期寫作中,發現自己在不同的創作階段,也伴隨著不同的創作狀態。新人時期,她寫一部作品須經漫長的構思,但隨著寫作能力進步,她得以「劍及履及、心到手到」,只要想好背景設定與故事邏輯,就可以很快地架構出一個故事,「這過程好比《傑克與魔豆》中迅速成長的藤蔓,我不必再等待豆苗緩緩發芽」。
在寫作手法與故事題材上,林佑儒力求突破,以提升作品的文學性;但凡寫過的模式或主題,即便暢銷,她也不願意再寫。正如某個教授談及學術傾向不是「很會唸書與考試」,而是「樂於面對未知、複雜、沒有立即答案的世界」,對任何新事物感到好奇興奮,繼而「廢寢忘食」;它不是「想到才做」,或「只出現於特定時間的興趣」。林佑儒說:「而所謂的『作家精神』,不光是『文筆好、很會寫』,更要對寫作心心念念:你是不是不斷地想要創作,有沒有不寫出來會很難過的主題,還有無論如何是否繼續挑戰自己……」
每本書每趟歷程,創作初心不變
不畏挑戰的林佑儒,是否考慮轉向成人文學領域,當個跨界作家呢?林佑儒篤定地說,自己最愛的還是兒童文學,而她會一直寫下去;畢竟,當初觸發她提筆寫作的,正是童書帶來的感動,讓年幼的她與成年的她久久無法忘懷。在她的作品中,讀者可見昔日還是小女孩的她,可見過去她教過的學生,也可見她自己兩個可愛的女兒;神奇的是,讀者也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身影,或是小時候暗戀的對象、閨蜜、兄弟與死對頭──是的,無論是她、編輯,或是你,我們都被這些故事召回各自的童年。
人生有不同進程,寫作也是。林佑儒回顧至今的創作生涯,悠悠地說:「每本書都是一段歷程,是回憶,也是紀錄。有些書,我現在回頭看,都會感到驚訝:哇!我現在可能寫不出這樣的句子了;而同樣的題材只要長存心中,即使經過了二十年,一旦用不同的故事結構去寫,作品就會不斷重生。」
如今,若有機會回到過去,林佑儒想對甫入文壇的自己說些什麼呢?她尋思片刻後說:「新人,常見的通病就是『缺乏現實感』,因為太想寫了,很難相對客觀地琢磨自己的作品;光有寫作的熱情,如果不了解出版環境或是市場現況,較容易努力錯方向。比如想拿完成的作品參加文學獎,卻連參賽的字數要求一點概念也沒有,一個勁兒地寫了二十萬字,那就繞了好大一個圈。」
「而且,寫作還是有資質差異。喜歡寫作跟出版作品,中間的距離其實滿遙遠的。」有些人心懷文學夢,也很能寫,卻沒有寫出多少作品;另有些人寫出了一些作品,其水準卻讓人不忍直言。所以,林佑儒鼓勵新人多參加文學獎(她本人也藉由文學獎出道),獎項猶如一個篩子,作品若能獲得評審青睞,也就意味著一定的寫作實力。「此外,目標若是出版作品,那就不能只是埋頭創作,也必須了解市場;但更重要的是,培養對好的文學作品的品味,才能寫出好作品。」
「……話雖如此,新人還是有優勢,那就是只要想寫,就會有動力去寫。」
林佑儒語畢,世界忽然靜默下來。
對談中的兩人終於走過遙往的過去與未來,回到了當下。街景越發清晰,隔著一扇明淨的大窗,雨勢不知不覺小得足見行人愜意的神情。那天在某間咖啡館,林佑儒的行李箱沉靜地靠在角落,看著主人與編輯含笑啜飲最後一口咖啡……
責任編輯:張惠鈞、曾邢家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