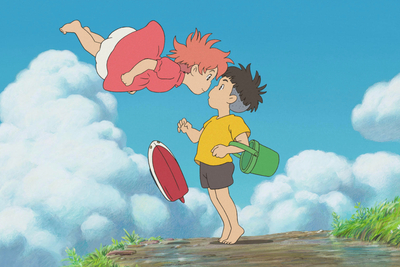文:蔡宜容(Dodoread都讀)
藥物成癮一度差點讓他非凡的事業中斷,我協助他逐漸戒除已經好幾年。如今,在一般情況下,他不再渴求這類人造刺激,不過,我知道惡魔並未死去,只是暫時睡著,我也知道,那只是淺眠,每當無所事事的時候,覺醒就近了。
—《福爾摩斯歸來記–消失的中後衛》,Sir Arthur Conan Doyle, Bantam Classic,本文作者自譯
※誰的悲傷?誰的迷亂?
在福爾摩斯探案中,《消失的中後衛》的知名度與討論度並不特別高,我卻對這篇十分在意,並不是因為案情如何曲折,或者破案過程神乎其技,事實上,福爾摩斯探案迷人之處從來不是這些。我在意的是,這個案件紀錄的開始與結束夾帶著無法逆轉的悲傷與迷亂,不只是文本人物的悲傷,更是作者與讀者的迷亂,或者可以這麼說,書寫與閱讀引發的悲傷與迷亂。
《消失的中後衛》刊出的時間是1904年,故事一開始,華生大夫就說這個案件約在七、八年前發生,推算回去,時間應該落在1894年福爾摩斯「復活」之後的三到四年,也就是1897年或1898年。如果根據美國藥物研究專家穆斯托的論文《古柯鹼的研究》(發表於美國醫學會期刊),文中他大膽假設福爾摩斯於1891-1894年間赴維也納接受佛洛伊德協助戒除藥癮,以時間點來看,確實符合華生大夫所寫的「逐漸戒除」。「藥物成癮一度差點讓他非凡的事業中斷」的說法更呼應穆斯托的推論:當時福爾摩斯對古柯鹼的依賴全面失控,面臨生死交關。不論華生大夫是否「真的」與佛洛伊德攜手,無論如何,是他陪著福爾摩斯走出死蔭的幽谷。幾年之後,他又在好友的身上看見死亡的陰影,淺眠的惡魔隨時都將覺醒,華生大夫束手無策,只能仰賴即時出現的古怪案件,多少轉移福爾摩斯的注意力。
華生大夫形容福爾摩斯的大腦「異常活躍」,如果沒有可堪挑戰的素材,「那將非常危險」,以致當他們接獲一封語無倫次的求助電報,燃起福爾摩斯的解謎興味,華生竟對尚未謀面的委託人由衷感謝,「因為對福爾摩斯狂亂的人生來說,危險的平靜比所有的暴風雨更要命。」
細看《消失的中後衛》前三段文字,華生大夫的目光幾乎全部聚焦在福爾摩斯的臉,看見肉眼可見的凹陷雙眼、憂鬱且莫測高深的神情,同時也看見肉眼不可見的,淺眠的惡魔。不誇張的說,這三段文字就是華生大夫的預知惡魔覺醒記事,但他並沒有說破。至於福爾摩斯,他顯然沒有說破華生大夫的沒有說破,畢竟,他從一截手臂的膚色與站姿就能推測出好醫生是從阿富汗解甲歸田的戰士。這樣的雙重不說破,反而將兩人最深的憂慮打出原形:惡魔這次沒醒,下次呢?福爾摩斯全集六十個故事中,僅五個故事提到福爾摩斯使用古柯鹼的習慣,在《血字的研究》、《四簽名》、《黃臉人》、《歪嘴的男人》中伴隨著華生大夫的不以為然、憂慮與憤怒,但是在《消失的中後衛》,華生大夫更多的是悲傷:幾年來的努力,很可能瞬間付諸流水,這一次惡魔出柙,他還能抓得住?難道要再向佛洛伊德求助?
福爾摩斯在《消失的中後衛》要尋找的人是劍橋大學橄欖球隊的選手,「全英國最好的中後衛」。辦案過程中得知一段淒美的、不能曝光的愛情故事,一旦宣稱破案,所有秘密公諸於世,堅貞癡情的中後衛將會一無所有,福爾摩斯會怎麼做呢?
福爾摩斯緊緊握著醫生的手。
「走吧,華生,」他說,於是我們離開那座悲傷的房子,走進冬日黯淡的日光中。
—《福爾摩斯歸來記–消失的中後衛》,Sir Arthur Conan Doyle, Bantam Classic,本文作者自譯
我讀著全文最後兩句,再一次感到《消失的中後衛》果真是一篇悲傷的故事,以悲傷開始,以悲傷結尾,甚至連破案現場的那棟房子都充滿悲傷⋯⋯然後我突然覺得哪裡不大對勁:福爾摩斯緊緊握著醫生的手。
※讀者的越位
不對啊,通篇故事由華生大夫主述,這句話卻明顯是透過第三者的觀點敘述,我在書裡書外混成一片的悲傷氛圍中,忍不住覺得好笑。也許心情激動的柯南・道爾爵士也被這樣的悲傷震動了,一時忘記被福爾摩斯緊緊握住的是「我」的手,「我」是華生大夫,「我」在事件裡,華生大夫不是旁觀第三者。
作者,同時也是讀者的柯南‧道爾在這裡同時現身,與其說這兩個角色擠掉了華生大夫,不如說他們三位一體了;與其說這是書寫的疏失,不如說這是作者與讀者同步越位,兩人四腳全踩在文本某一個人物身上⋯⋯啊,讀者的越位!然後我想起自己如何列出《消失的中後衛》的時間軸,試圖從中看見華生大夫的悲傷,這個過程豈非也是讀者的越位?
我結合出版年份與華生大夫提供的紀錄,推算出這則案件可能發生的時間,接著援引穆斯托教授論文中的推測,證明福爾摩斯藥癮一度失控,瀕臨生死關頭,數年之後危機再起,正因為有過之前的痛苦經驗,這一回華生大夫才會憂懼更深,悲傷更甚⋯⋯。
我的時間軸線索分別來自現實與文本中的時間,我的推論依據來自現實的期刊論文、論文中對文本人物的遭遇提出的假設,當然還包括文本中白紙黑字的證據⋯⋯做為讀者,我畫出來的文本時間軸至少存在兩個平行時空;作為讀者,我理解文本的線索根本無法僅限於文本;作為讀者;我在自己知道之前已經開始進行各種越位,我不但把其他福爾摩斯探案中的情節帶進我的閱讀,我還把存在穆斯特推理中的佛洛伊德帶進了我的閱讀,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橫衝直撞⋯⋯我想,如果消失的劍橋中後衛最後選擇人間蒸發,也許我可以客串代打也未必可知。畢竟,做為讀者,我經常逾越自己的位置,出現在限制之外的位置,我也經常帶著其他文本逾越它們的位置,讓他們出現在限制之外的位置⋯⋯但是,哪一個讀者不是這樣呢?讀者的越位與橄欖球越位最大的不同在於,後者越位有規則可循,前者只管進攻,就算是對手的越位陷阱也照踩不誤。
也許可以把讀者越位的這股勁兒看成與書籍的秩序衝撞的力道,這股力道接近法國學者夏提葉所說的「閱讀的自由」。它可以扭轉限制,「並形塑本應受到抑制的新意涵,在秩序的施加與讀者的挪用之間,以及在被逾越的限制和受到束縛的自由之間的辯證關係⋯⋯」挪用也罷,越位也罷,都是一種脫離,一種脫離被監管、要長出自己樣子的欲望。讀者都是這樣的吧?我知道一概而論的危險,我知道舉證的必要,這時也該把法官請出來了。
※法官大人,我有異議
1977年,穆斯托對《百分之七的溶液》的作者、出版社、電影製作、發行方提出侵權訴訟,聲稱該書部分情節涉及複製他的論文內容,主要聚焦於《最後一案》中福爾摩斯詐死的原因。穆斯托認為福爾摩斯並非為了打擊犯罪隱遁三年,而是因為藥癮失控,華生大夫連哄帶騙把他架到維也納,在佛洛伊德的幫助下成功戒除藥癮。《百分之七的溶液》的故事有著類似的架構。穆斯托最後敗訴,理由之一是很難證明「想法」的原創性,而且他的想法衍生自《最後一案》,偏偏這本書的版權已經進入公共領域,不受著作權保護,更何況從它衍生出來的「想法」。
穆斯托閱讀福爾摩斯,推理福爾摩斯,上窮碧落,穿越虛實⋯⋯到頭來,這一切畢竟不是福爾摩斯的,也不是他的。
法官說的興起,談起讀者來了。他說從撰寫目的與讀者層面來說,論文與小說並不存在相似性。意思是刊登在學術期刊上的論文,就算引用文本人物,目的仍是學術。小說就是小說,福爾摩斯書迷寫仿作的目的自然是要吸引其他福爾摩斯書迷。
法官大人,我有異議。
首先,學術論文的目的可以不只是學術,閱讀學術論文的目的當然也可以不只是學術。畢飛宇在他的《小說課》提到自己讀不懂《時間簡史》,卻不減喜愛,「每次讀完都覺得自己在旅遊,在西藏,在新疆,在一輩子都登不上的雪山上。」他又舉了畢卡索的例子。畢卡索喜讀愛因斯坦,「當我讀愛因斯坦寫的一本物理書,我啥也沒弄明白,不過也沒關係,他讓我明白了別的東西。」
所以,法官大人,書寫學術論文可以為了爬梳十九世紀古柯鹼簡史,也可以為了向熱愛的福爾摩斯致意,兩者並不違和。至於閱讀這篇學術論文的讀者如我,我在文章裡讀到英美十九世紀古柯鹼的應用,讀到好醫生為了把名偵探從身心死亡的邊緣救出來,只差沒有偷拐搶騙,一路殺到維也納,應是把現實世界的佛洛伊德給拉進來⋯⋯你記得上一次這麼拚命救人的是誰?直闖冥界搶救妻子的奧菲斯?想也不想躍入絕情谷,寧可跟姑姑一起死的楊過?捨命搶救少女瑪蒂達的殺手里昂?我在穆斯托的學術論文讀到同樣令人震動的心意。至於梅爾小說訴求的讀者,我相信規劃目標客層有其必要性,但是閱讀是一種看似受控,其實非常失控的的行為,它確實存在歪打正著、正打歪著的可能性,我希望《福爾摩斯是誰的?3-1,3-2, 3-3》一定程度說明了這一點。
※參考資料
‧邦薩爾法官判決書
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FSupp/434/32/1416913/
‧《小說課》,畢飛宇,九歌出版社
‧《消失的中後衛》,收錄在《福爾摩斯歸來記》,作者是亞瑟‧柯南‧道爾,選用版本為Bantam Classic,文中引文為蔡宜容翻譯
‧《書籍的秩序》,夏提葉,謝柏暉譯,聯經出版社
一點說明:我買不到穆斯托的論文《古柯鹼的研究》(A Study of Cocaine),網路上搜尋到許多片段,拼湊著讀,網路上也有別人引述這篇文章的文章,一起拼湊著讀。
責任編輯:王予彤、黃懿蓉、李季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