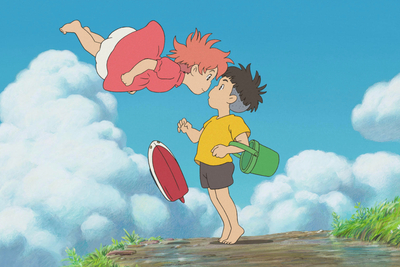文:蔡宜容(Dodoread都讀)
※從兩則不相關的線索談起
線索1:2010年德國電影導演韋納‧荷索成立「無賴電影學院」(Rogue Film School),做為一個回應熱愛電影工作者的學習途徑與場所。入學許可、培訓課程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每期具體課綱、時間不確定。這是當然。任何想要親近荷索的學員都不至於懷抱「正常」教育訓練的期待。總之,荷索認為自己與學員的關係更像是中世紀木匠師傅與學徒之間的關係,學校名為「無賴」意在挑釁,你得有足夠的膽量才能死咬著夢想不鬆口,膽小怕事的別來,心裡火在燒的、對詩有點感覺的,願意學開鎖、偽造拍攝許可證的人具備報名資格,還得會說故事,「能讓四歲小孩聽得目不轉睛」那種程度⋯⋯。
開出這樣入學條件的學院播放哪些電影呢?訪問者提出問題。荷索反問「我說過要放電影嗎?」荷索說:「我只說一件事:看書,除了看書還是看書⋯⋯不看書你永遠成不了電影人。」他還開了一張強制書單,裡面每一本書都跟電影無關,作者包括維吉爾、拉伯雷與海明威,他並且推薦《華倫委員會報告》(Warren Commission Report),那是甘乃迪遇刺事件的官方調查報告。荷索說這份文件講了一個「很特別的犯罪故事,有很強的敘事力量與令人信服的邏輯性。」
線索2:《冷戰諜魂》、《裁縫、鍋匠、士兵與間諜》的作者約翰‧勒卡雷在自傳提到,他這輩子接受過最嚴格的寫作訓練並非來自學校,而是他曾經任職的軍情五處總部頂樓「那些受過古典教育的高階官員」。這些人對報告中結構不連貫的句子與贅字十分不屑,勒卡雷說他交手過的編輯都沒這嚴苛,「或者應該說他們都沒這麼準確。」
荷索在《華倫委員會報告》裡讀到的應該不只是官方說法,恐怕更是官方為了完成各種說法,必須鋪陳出一則上下連貫,足以說服人的故事;或者可以說,荷索看見故事形成的脈絡。勒卡雷做為情報人員,他的調查報告必須服膺某種特殊目的,為了合情合理合法達到目的,報告的邏輯必須令人信服,敘事必須簡潔有力;或者可以說,勒卡雷根必須據調查線索,編輯並創造出可以交差的故事。
無論如何,荷索與勒卡雷都沒有提到報告的真實性,他們使用的字眼分別是「使人信服」與「意思要正確」。報告裡交代的與其說是「真相」,不如說是「意思正確,使人信服」的故事。
如果說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扮演偵探的角色,抽絲剝繭,拼湊出屬於自己的真相。那麼,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同時又是全案關鍵證人,必須接受偵探三天兩頭的騷擾:「有沒有注意到什麼不尋常的狀況?如果想到任何事情,儘管再瑣碎、再不相關⋯⋯請務必跟我聯絡。」
喜歡偵探小說、警匪劇集的人都知道,「案件」不存在毫無關聯的線索,斑斑跡證都攤在你眼皮子底下,光是看是不夠的,你必須觀察。如今我們也都知道,經過時間醞釀,有時候「看見」會轉化成「觀察」:你以為自己視而不見的東西,可能透過刻意或不經意的聯想重新浮現。
線索1與線索2看似與福爾摩斯毫無關聯,竟是某種觸發閱讀連線的紅絲繩,牽動我奔向名偵探與好醫生;於是,證人蔡宜容聯絡偵探蔡宜容,重返案件現場。
※古柯鹼的研究–當福爾摩斯遇見佛洛伊德
福爾摩斯全集包括四個長篇、五十六則短篇探案,某種程度來說,可以看作華生大夫為名偵探所寫的結案報告(其中兩則短篇為福爾摩斯主述)。報告中除了詳述案情緣由、偵辦過程、破案手法,以及涉案人側寫,當然更包括華生對福爾摩斯的觀察與情感。百餘年來,讀者從這套結案報告中讀到許多訊息,從訊息中衍生出更多聯想與故事,其中包括美國藥物政策專家大衛‧富蘭克林‧穆斯托(David F. Musto 1936–2010)與美國作家尼可拉斯‧梅爾(Nicholas Meyer 1945–)。
穆斯托是深具影響力的美國藥物歷史與政策研究學者,在卡特政府時期應聘為國家顧問。穆斯托任教於耶魯大學醫學院,並且是該校「福爾摩斯社團」創辦人。是的,穆斯托是熱烈的福爾摩斯書迷, 他甚至參加了「貝克街游擊隊」(The Baker Street Irregulars,簡稱BSI)。BSI是美國小說家、記者克里斯多福‧莫利(Christopher Morley)1934年創辦的男性菁英社團,團名來自書中一群幫福爾摩斯蒐集情報的街頭少年。BSI不定期聚會、出刊,討論文學、藝術與福爾摩斯,直到1991年才出現兩位女性團員。
穆斯托不但是熱情書迷,更是一個有趣的讀者,他不只在福爾摩斯全集裡讀到福爾摩斯,更在別人讀不到,或者還來不及讀到,或者讀到了卻八字還沒理出一撇的地方讀到福爾摩斯,他甚至為此寫了一篇論文刊登在《美國醫學會期刊》(Volume 204 (1) – Apr 1, 1968),論文標題為:古柯鹼的研究:夏洛克‧福爾摩斯與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A Study in Cocaine: Sherlock Holmes and Sigmund Freud)。論文副標題不言自明,主標題「古柯鹼的研究A Study in Cocaine」更是直接向福爾摩斯第一案「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致意。
穆斯托爬梳十九世紀古柯鹼簡史,討論這種「精神藥物」如何在西方社會引起重視。穆斯托的切入點是福爾摩斯與佛洛伊德,藉由古柯鹼與兩人的關係,進一步檢視此藥物對文學與科學的影響。穆斯托試圖說明,關於古柯鹼的研究,不論各種評估如何客觀,都很容易湮沒在個人狂熱的追求中,就算取得大量證據,所謂「正確的」論斷何等困難!福爾摩斯是遊走虛實界線的頭號文本人物,佛洛伊德是一手模糊文學與科學界線的先驅⋯⋯找來十九世紀雙巨頭揭開學術論文序幕,這個起手式也太讓人血脈賁張!
穆斯托論文中提到,十九世紀末的維也納穩坐世界眼科手術王位。奧地利眼科醫生Carl Koller在 1884年一場手術中成功使用新式麻醉藥物引發關注。該麻醉藥物提煉自安地斯山脈一種植物的葉子:古柯葉,當時西方科學界對此應用並不熟悉。Koller的靈感來自他的年輕同事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時年二十八歲的佛洛伊德告訴Koller,他讓一位病患服用古柯鹼,病患出現舌頭麻痺的症狀,嘴唇也失去感覺。Koller本著科學家的實驗精神,回到實驗室後在自己眼睛裡點了幾滴,接著用別針戳一下,毫‧無‧感‧覺!Koller因此開發出局部麻醉藥物,特別適合眼科手術使用,一時間,自世界各地前往維也納取經的醫生絡繹於途。穆斯托指出,佛洛伊德簡直對古柯鹼著迷,積極研究相關副作用與美國的使用情況。
談到十九世紀,談到古柯鹼,偵探小說讀者很難不想到福爾摩斯。透過華生大夫的貼身紀錄,讀者對名偵探布滿針孔的手臂與濃度百分之七的古柯鹼溶劑再熟悉不過;讀者也都目睹了福爾摩斯異於常人的作息:若不是近乎狂躁的投入工作,就是陷入迷茫昏沉的藥效。穆斯托作為資深且狂熱的書迷當然知道,不但知道,他還做出大膽推測,他認為《最後一案》中福爾摩斯與莫里亞提教授一同墜亡雷陣巴赫瀑布,其實另有隱情。
世人只知1891年四月結束的時候,這個世界失去了獨一無二的諮詢偵探,直到1894年福爾摩斯以《空屋奇案》歸來,讀者普大喜奔,至於消失的三年期間,名偵探在哪裡?做什麼?福爾摩斯僅僅用一小段敘述讓華生知道,他去了西藏,挪威、波斯、法國,解決幾個莫里亞提餘黨,做了一些煤焦油衍生物研究⋯⋯文本世界三年空窗成為許多fanfiction大做文章的肥沃土地,同時也讓讀者穆斯托以古柯鹼為觸媒,找到福爾摩斯與佛洛伊德跨時空連結的可能。穆斯托的推論如下:名偵探藥癮失控→好醫生斷然出手→聯絡精神分析開山祖師→安排名偵探赴維也納接受治療。這個推論的時間點一定程度呼應佛洛伊德對古柯鹼研究的強烈興趣,具備發展成一篇同人文或衍生小說的雛型,當然,穆斯托並沒有朝這裡發展,他做的畢竟是古柯鹼研究。
※推理福爾摩斯…誰的推理?推理是誰的?
接下來,且讓我們釐清幾個時間點。
1894這一年,死域歸來的福爾摩斯四十歲,已經在維也納嶄露頭角的佛洛依德三十八歲。1968這一年,讀者穆斯托將文本宇宙與現實世界並置,為學術文章切出朦朧的故事線,同時引發更多讀者激昂的想像。1974這一年,美國作家尼可拉斯‧梅爾出版福爾摩斯仿作《百分之七的溶液》,書籍上市後立刻攻占暢銷榜,並於1976年翻拍同名電影,由梅爾親自擔任編劇、導演。梅爾在書後致謝文提及,創作的主要靈感來源之一即為穆斯托的論文。
《百分之七的溶液》中的華生大夫半哄半騙安排一趟維也納之旅,讓身心飽受古柯鹼摧殘的福爾摩斯接受佛洛伊德治療。福爾摩斯並且接受佛洛伊德催眠,終於說出自己的心魔:母親與他的數學家教莫里亞提畸戀,父親射殺母親後自殺。佛洛依德讓福爾摩斯挖出自己深埋在潛意識的記憶,一舉偵破名偵探性格的謎團,包括他為什麼選擇退出正常世界、為什麼不喜歡女人、為什麼將微不足道的莫里亞提視為「犯罪界的拿破崙」。總之,一切都有了「合理」解答,童年的壓抑與複雜的罪咎感首度釋放,進入催眠狀態的名偵探甚至「泣不成聲」!佛洛伊德因此得到華生的讚嘆:「你才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偵探。」
從小說主要情節看來,穆斯托的推論確實奠定全書基本架構。至於福爾摩斯父母與家教之間的情感糾葛,則分別來自幾位赫赫有名大書迷的推論,包括威廉‧貝林哥(William S. Baring-Gould)與崔佛‧霍爾(Trevor Hall)。梅爾也在致謝文中提及這些「主要靈感來源」。
1977年,穆斯托對《百分之七的溶液》的作者、出版社、電影製作、發行方提出侵權訴訟,聲稱該書部分情節涉及複製他的論文內容,包括字面與非字面釋義。幾經拉鋸,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駁回穆斯托所訴。因為閱讀福爾摩斯、推論福爾摩斯、書寫福爾摩斯衍生的所有權之爭如何歸屬?主審邦薩爾法官寫出一篇挺有意思的判決書。
判決書一開始就引用收錄在企鵝版《福爾摩斯回憶錄》中《黃臉人》的一段話:「除了偶爾使用古柯鹼,福爾摩斯並無其他惡習,而且只有在沒有案件、報紙新聞又無趣的時候,他才會使用藥物作為對單調生活的一種抗議。」法官認為這段文字可以作為訴訟案的背景資料,並且簡述原告聲稱被侵權的論文題要,以及被告涉及侵權的小說概略,接著說明本案著作權可以明確釐清的部分,但是要證明複製侵權,原告必須提出「實質相似性」,兩造針對這點激烈交鋒。
穆斯托強烈主張自己論文中幾個基本推論不斷在梅爾的小說中出現。包括《最後一案》中有關福爾摩斯消失三年的真正原因,讀者都被柯南‧道爾誤導、在《最後一案》中華生判斷福爾摩斯因為古柯鹼上癮導致妄想、佛洛伊德成功幫助福爾摩斯戒除藥癮,福爾摩斯則展現個人推理風格做為回報…法官指出,著作權法通常只針對作品中原創元素提供保護,如果受保護的作品本身即衍生自其他作品,一旦「其他作品」進入公共領域,衍生性作品未必適用著作權保護法。以穆斯托控告梅爾一案為例,柯南‧道爾《最後一案》已經進入公共領域。再者,小說與論文唯一相似之處只是一個「想法」:福爾摩斯用藥成癮,佛洛伊德成功幫他戒除。除非能夠證明「想法」的原創性,否則不受著作權法保護。法官進一步指出,從撰寫目的與訴求讀者層面來說,論文與小說並不存在相似性。法官說,穆斯托的論文雖然有些玩笑意味,卻是刊登在專業期刊上的論文,目的是向讀者介紹十九世紀古柯鹼使用。梅爾的小說設定則是重新編輯華生大夫未發表的手稿,訴求的對象自然是福爾摩斯的追隨者。
都說到這個份上,穆斯托肯定無法勝訴了。
※普通讀者的法庭記錄閱讀樂趣
英美讀者對法庭記錄或判決書的閱讀趣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1820年代,英國泰晤士報第三版可不是要聞版或清涼圖片版,而是法庭審判實錄。以1828年2月5日為例,當天一位維持社區善良風俗的教會官員出庭應訊,做證教區一對青年男女周日傍晚在教堂裡行為不當。以下片段節錄自”Tickle the Public”:
法官:他們當時在做什麼?
糾察官:面對面笑開了花。
法官:就這樣?
糾察官:不,庭上,他們可是放開膽子了。
法官:怎麼放開膽子?
糾察官:手牽手說話,情話綿綿,蜜裡調油。
(法官要求具體說明,糾察官說他沒聽見。)
法官:你離他們很遠?
糾察官:不,很近,大人,不過我穿便服,他們沒認出我。
法官:教區居民曾經提出抱怨嗎?
糾察官:沒有,大人。
法官:他們在一起說了多久話?
糾察官:將近一分鐘。
法官:將近一分鐘!五十又過個幾秒,連句話都沒法說完整!好吧,然後你做了什麼?
糾察官:我活逮他們,將他們拖出教堂,送進觀察所。
法官:你關了他們一整晚?
糾察官:是的。
法官:我認為你的行動非常輕率⋯⋯被告,你們當庭釋放。
糾察官:求您了,法官大人。
法官:我不再回應。全案終結。
作者Matthew Engel形容這篇法庭實錄完全不輸狄更斯的手筆!法庭紀錄的文學趣味豈止一端。十八世紀英裔美籍作者Thomas Paine的《理性年代》倡議自然神論,直指神啟卻必須透過他人口頭或文字傳達的矛盾性,強調「我心即教堂」,這樣的觀念在當時的氛圍下當然是禁書,十九世紀英國出版商卡萊爾為了出版這本書先後入獄九次,其中一次自我答辯時朗誦全書,歷時十二小時,因為他要確保全書內容成為「公開記錄」!十九世紀福樓拜的小說《包法利夫人》與二十世紀艾倫‧金斯堡的長詩《嚎叫》都曾因為傷風敗俗被告上法庭,正反方引用文本進行詮釋,不論是追究單字單詞的意義,或者爭論文意引發的想像⋯⋯無疑都是法庭版文學批評論戰,審理法官必須據以做出「禁與不禁」、「是否傷風敗俗」的判定,普通讀者如我卻在法庭攻防與法官判決書中讀到文本與現實的交錯與跨越,讀者與作者的越位攻防,最終指向文學與閱讀究竟是什麼的思考。
下一篇,讓我們回到邦薩爾法官的判決書,從判決書再啟程。因為熱愛福爾摩斯,因為閱讀福爾摩斯產生的顛倒夢想⋯⋯究竟是誰的?讀者證人蔡宜容與讀者偵探蔡宜容重返《最後一案》現場的結案報告書終於也要走向3-3。
※參考資料
‧《陸上行舟:赫爾佐格談電影》,赫爾佐格、保羅‧克羅寧/著,黃淵/譯,上海三聯書局(此書為簡體版,『赫爾佐格』台譯多為『荷索』)
‧《此生如鴿:間諜小說大師勒卡雷的38個人生片羽》,勒卡雷/著,李靜宜/譯,木馬文化
‧邦薩爾法官判決書
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FSupp/434/32/1416913/
‧Tickle the Public—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Popular Press, Matthew Engel, Indigo
‧《百分之七的溶液》,尼可拉斯‧梅爾/著,卓妙容/譯,臉譜出版
‧福爾摩斯的生日是1854年1月6日。1854年是根據文本資料反推,雖不中亦不遠矣。1月6日的說法來自「貝克街游擊隊」(The Baker Street Irregulars)創辦人克里斯多福‧莫利(Christopher Morley),1月6日是主顯節,主顯節是基督徒慶祝耶穌降生為人後,首次顯露給外邦人的日子。小範圍來說,外邦人指的是東方三賢士,大範圍來說,所有世人皆為外邦人。莫利不是普通瘋狂,但哪個福爾摩斯書迷不是?或者,哪個書迷不是?
責任編輯:王予彤、黃懿蓉、李季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