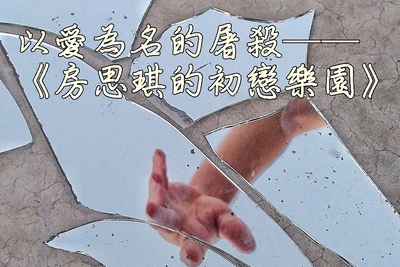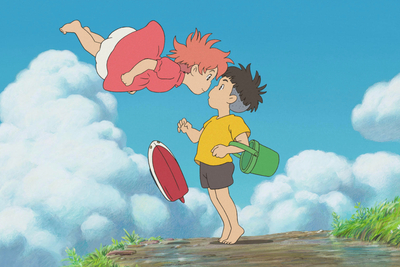文/鄭仲珈
圖/取材自繪本內頁
我們,或許都是世界裡的「異鄉人」。那是身處其中卻又疏離的感受,有時彷彿能穿越時間的縫隙,看見存在於生活的背面。
在《巨人》裡,人類在他緩慢的步伐下顯得渺小而匆忙;《遷徙者》的流離,讓人重新思索「異鄉」與「邊界」的意涵;而在《奧圖:書裡的熊》中,小熊跨出書頁,遇見了新的故事與朋友。這些角色如同漂泊的小船,也像是觀察者。他們用不同的眼光訴說著:有時不屬於某處,是孤獨、是自由,也是帶來希望的開始。
——七月,讓我們透過這些繪本的眼睛,看見書頁之中的異鄉。
他們眼裡的世界是什麼模樣呢?或許能夠問一問那個剛剛才睡醒的大個子
巨人醒了。
如同往常一樣,他打了一個巨大的哈欠,世界在他的呼吸間震顫著,就連遠方的湖面也揚起漣漪。沒有人注意到他的甦醒,就像在清晨時,我們很少能夠專注地定睛在晨光裡布滿的塵埃上。巨人不慌不忙地前行,當他跨出幾步,便已越過山谷,走入人類的世界。
《巨人(Milzis)》是捷克作家 Tereza Šiklová 的首部出版繪本。故事中描繪了一位每兩年才甦醒一次的巨人。這次,他在春天的第一道暖陽下醒來,他開始了嶄新的一天,如同人類一樣,他必須外出工作。巨人緩慢、沉穩的世界中沒有匆促的節奏。當讀著跟隨著巨人的腳步,便看見他與人類之間尺度上不可思議的差異,例如:巨人所邁出的步幅、肚子餓時發出雷鳴般的咕嚕聲響、口渴時幾乎要把湖水一飲而盡的水量。

對巨人而言,時間的流動沒有產生太大的變化,當他穿梭於城鎮之中,看到的是蜜蜂般殷勤地、如同滄海一粟的人類,午休時間總是匆匆忙忙地趕著回到工作崗位的上班族、焦急地等待著交通號誌的行人。這座擁擠的城市,讓巨人感到無比困倦。

最終,巨人決定動身離開人類所居住的城市。
對他來說,回到家的距離不過是幾步之遙。他悠然地走著,人類眼中瞬息萬變的景色,在他看來像一幅幅巨大的定格畫面。從巨人的視角,人類的步伐如同螞蟻搬運細沙般細碎;而對人類來說,計算沙灘上的沙粒,同樣困難。
故事的尾聲中,Tereza Šiklová 寫道:「試著用巨人的角度看看這個世界吧!也許一切將不再困難。」這句話讓人想起卡繆《異鄉人》中的主角「我」,「我」雖身處人群之中,卻總帶著疏離感,像一個從遙遠宇宙回望地球的旅人,冷靜卻清晰地看見一切。透過「我」既置身其中,又不受社會規範制約的存在,直面著人生的荒謬。
回到《巨人》這部繪本中,巨人與人類之間的差異,製造出了新的視埠。巨人的散步、作息與觀察,正是一種純粹的存在。沒有功利與效率的枷鎖,在繁忙與喧囂的日子裡,他是旁觀者,卻更清楚地看見人們的執著與捆縛。

「試著用巨人的角度看看世界」這樣的念頭,或許也可能同時隱身著另一層意涵——在命運面前,人們依然能夠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態度。一如《異鄉人》中,與死亡比鄰的主角所言:「在布滿預兆與星星的夜空下,我第一次敞開心胸,欣然接受這世界溫柔的冷漠。」脫離情感風暴的中心,走在那條既陌生又熟悉的道路上,看著沿途發生的一切,當平靜的時刻來臨,也許,正是讓我們更清晰地看見自身與世界的契機。就像是繪本《巨人》裡,城市之中偶爾出現在畫面裡頭的——那空白而巨大的身影,清明而皎潔。

《거인 Milzis》
作者:Tereza Šiklová
出版社:Atnoonbooks(2024年) 1

在《遷徙者》的開頭,一片寂靜的大地上,只有一隻藍色的大鳥與披著花衫的骨頭。骨頭看見一只被遺留下來的手提箱,他小心翼翼地拾起,跟上前方的一群動物隊伍。牠們提著大大小小的包袱,看起來正要前往遠方。當骨頭上前,似乎在詢問遺失物主人的下落,但轉過身的動物們,一個個的眼中都是沒有瞳孔的,如同骷髏般失了神,沒有光,也沒有方向,只有零星幾隻小動物,眼底還存留著微弱的神色。

骨頭就這麼開始跟著動物們前行。然而,這些動物究竟要去向何處呢?翻開下一頁,在混沌的景色之中,他們開始將一件件物品從行囊裡取出,圍繞在一起,佈置起一方天地。那是家嗎?抑或只是暫時的庇護所?這些動物們似乎沒有了物種的分界,鵝與兔子、青蛙與狐狸、小驢與獅子,原有的領地與秩序被打破,當他們緊緊相依時,黑暗中有什麼東西無聲無息地長出了色彩。
骨頭,此刻的你又在何處呢?

在地平線的另一端,或者是另一個平行世界,骨頭與一隻北極熊分立於畫面的兩側。這隻北極熊不同於遷徙的動物隊伍,他四肢著地且未著衣物,只有自然生長的毛皮。大熊的身後草木欣欣向榮,但骨頭背後仍是一片寂寥。骨頭舉起一隻枯木,使我想起伊甸園的故事:在蛇的引誘下,亞當與夏娃偷嚐禁果,從此墜入塵世,在人的善與惡之間沉淪、擺盪。在《遷徙者》裡,看似逃離什麼的動物們,也彷彿是人世間的亞當與夏娃。他們如同人類般站立,對物品抱有執念,穿戴著蔽體的服裝。不盡相同的是,他們彼此互助,沒有物種之分,也沒有國界。
在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鄉愁》中,來自俄羅斯的詩人主角與作為其翻譯的女子之間有著一段對白:
詩人:你在看什麼呢?
翻譯的女子:塔可夫斯基的書。
詩人:俄文的?
翻譯的女子:不,是譯本,翻譯得很好。
詩人:扔掉它吧!
翻譯的女子:為什麼?譯者是位優秀的詩人。
詩人:詩是不可翻譯的,和所有藝術一樣。
翻譯的女子:也許你說得對。詩是無法翻譯的,但音樂呢?音樂是相通的。
詩人:(哼著歌)
翻譯的女子:請問這是什麼呢?
詩人:俄國音樂。
翻譯的女子:那我們怎樣才能理解托爾斯泰、普希金,從而理解俄國?
詩人:你們沒有人理解俄羅斯。
翻譯的女子:如果不通過但丁、佩脫拉克、馬基維利,你也無法理解義大利。
詩人:可憐的人類做不到。
翻譯的女子:那我們如何理解彼此呢?
詩人:廢除邊界。
翻譯的女子:什麼的邊界?
詩人:國家的邊界。
《鄉愁》中的這段對白,總讓人聯想起當前的時局,心緒不寧。所謂身處「異鄉」的異鄉,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是國與國的分界、無法產生交集的語言,還是人類永遠無法觸碰的他者內心呢?
《遷徙者》的終幕裡,流離失所的動物們最終坐上了方舟,遠渡重洋。過程裡,動物們失去了同伴,也有沉入海中無法帶走的身外物,但他們仍舊牽著彼此的手。在哀悼逝去後,他們的前方出現的是繁花盛開的彼岸,如同骨頭見到的北極熊世界。
我想像著,在《遷徙者》中,骨頭不僅僅是引領亡靈的死神,也是舟楫,牽引著這些動物穿越「人類世2」,還至本處。

在故事開頭出現的手提箱,此刻又緊緊握在哪個小動物的手心中呢?
闔上書本的那一刻,想起動物們為了彼此的失去而感到哀慼,卻在險惡之中始終沒有鬆開手。也許此時他們正身處於未知的國度,看不清前路的方向,但在看不見的地方,會有希望紮根,建立起一個新的原鄉。
在這裡,沒有人是異鄉人,也不再感到孤獨。

《遷徙者 MIGRANTES》
作者:渡邊伊莎(Issa Watanabe)
出版社:大塊文化(2023年)
當你需要夥伴時,請試著將這隻書裡的小熊放進你胸前的口袋裡
你曾想像過,有一天書裡的角色,會站在你的面前向你揮手嗎?
「奧圖是書裡的熊。」

是的!奧圖是一隻來自書裡的熊。這隻小熊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在沒有人注意的時候,奧圖會跑到外面的世界四處探險、閱讀他喜歡的故事,甚至偷偷練習寫作。

有一天,奧圖的小主人搬走了。他不喜歡孤零零地待在空蕩蕩的房間裡,於是下定決心,做好萬全準備,展開一場屬於自己的冒險旅程。
奧圖穿梭在人類的城市之間:高聳的房子、來往的人潮、呼嘯的車陣,每一樣東西都巨大得令人望而生畏。誰都沒有發現,在這條街道上,竟有一隻小小的、來自圖畫書裡的熊正悄悄經過。這一切讓奧圖覺得自己如此渺小、孤單,他開始深深想念那本屬於他的書——也就是奧圖的家。

就在奧圖感到沮喪的時刻,他發現了一處散發著光亮的大屋子,那是被人類稱為「圖書館」的地方。裡頭收藏著好多的書,他甚至遇見了來自其他書裡的另一隻小熊,以及各式各樣的角色。
在這個新世界裡,奧圖第一次擁有了朋友,並展開新的生活。奧圖依舊喜歡閱讀的故事、練習寫作,也嘗試著許多新的挑戰。不同的是,這一次他不再感到孤單。他有一群陪著他玩耍、探險的夥伴,也有許多喜愛他的讀者。現在,奧圖成為了一隻「世界上最快樂的書裡的熊」。
《奧圖:書裡的熊》描繪著一則純真可愛的故事。奧圖彷彿象徵著現實世界中的每一個生命,在日復一日的時光裏頭,我們各自編織著屬於自己的軌跡。有時,也會有那些孤獨與無力的時刻。但也許在下一個轉角,我們就能遇見一位志同道合的夥伴,陪我們走過接下來的冒險旅程。
當你正身處於全然陌生的領域,感到自己像是一艘漂流著搖搖欲墜的紙船時,也許,你該翻開這本書,將奧圖放進胸前的口袋中。或許,他會在你的耳邊,向你訴說著他所經歷的一切⋯⋯。

《奧圖:書裡的熊 Otto The Book Bear》
作者:凱蒂.克萊明森(Katie Cleminson)
出版社:米奇巴克(2024年)
1 手邊取得的繪本是購自童里的韓文版《거인》。
2 人類世(Anthropocene):意指在人類的出現後,其活動影響著地球生態與地質變化的層面,其中包含生態毀壞、氣候變遷、都市化、工業污染等;目前人類世仍是一個尚未被正式標示出起始年代的地質概念。書寫這一段落時,想像著當動物們經過人類所造就的破壞與界線,最終回到生命的源頭或自然的意象。
|編輯悄悄話|
選定七月的主題「異鄉人」時,思考著許多切入的角度,結果不知不覺就寫成了一篇五味雜陳的推薦(有些不好意思的)。閱讀《遷徙者》時,看起作者在序言中提及的電影《鸛鳥踟躕》,內容與當今的世界局勢不謀而合,一不小心就掉入了思緒的漩渦之中。明明是些可愛的繪本,卻越讀越覺得憂傷(像是《巨人》與《奧圖:書裡的熊》),甚至意外染上了重感冒,情緒真是奇妙的東西呢(笑)。
小時候常在日本動畫裡聽到一句話:「夏天感冒的都是笨蛋!」邊寫著這段話時,在螢幕前打了個噴嚏。
願 大家都能避開酷暑與感冒,平安地度過這個夏天!
責任編輯:周燕雯、鄭仲珈、李品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