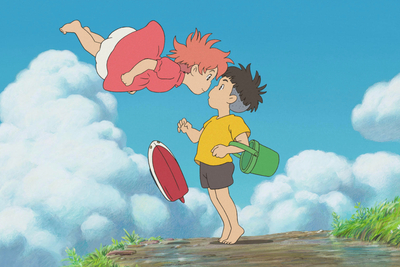文:吳肇祈
圖畫書中的誤聽,除由不理解造成,例如將「葬禮」(Beerdigung)聽成「藏起」(Begradigung,原意為「拉直;矯直」)的小男孩布魯諾(註1);或表達對方的忽略與不在乎,像是將「小象」(elephant)聽成「小香」(Ella)的忙碌搬家中的媽媽(註2);另外還有為了創造樂趣,作為語言聲音與意義上的一種文字遊戲(word play)。這類誤聽常以「音譯為主、意譯為輔」的方式進行翻譯,主要還是不想捨去「造成誤聽」或「誤聽導致」的聲音效果。
羅倫斯.波利(Lorenz Pauli,1967 –)作品《狐狸愛上圖書館》(註3)便是一本從書名就向讀者展示聲音「誤聽」效果的圖畫書。《狐狸愛上圖書館》源語書名Pippilothek??? Eine Bibliothek wirkt Wunder,其中「Pippilothek」正是「Bibliothek(圖書館)」一詞的誤聽。圖畫書一開始描述了一隻一路追趕老鼠的狐狸,尾隨老鼠的逃亡路線進入了圖書館。老鼠利用圖書館公規與特性,以及狐狸對於圖書館的一無所知,約制狐狸的追捕行為——圖書館必須保持安靜,並且圖書館內所有的東西均非私有,故此身處圖書館的老鼠自然也不屬於牠的天敵。
(源語文本)
»Hier kann man alles nur ausleihen. Und ICH gehöre dir ganz sicher
nicht. Das ist kein Jagdgebiet, sondern eine Bibliothek. «
»Eine Pippi... was?«, fragt der Fuchs.
»Eine Bibliothek«, sagt die Maus.
Der Fuchs schaut sich um: »Was ist eine Pippilothek? «
(正體中文譯本)
「這裡的東西只能用借的,所以我不可能是你的。
這裡不是打獵的地方,是圖書館。」
「讀⋯⋯什麼啊?」狐狸問。
「圖書館。」老鼠回答。
狐狸看了看四周,說:「什麼是圖書館?」
這個段落點出了圖畫書一大特點,即「Pippilothek」一字的由來。原屬於「Jagdgebiet (狩獵場/正體中文譯本譯作:「打獵的地方」)」的狐狸,初次踏入「Bibliothek(圖書館)」,所以對於「Bibliothek」一詞不甚了解,產生誤聽導致錯誤發音也在情理之中。此一文本環節在於顯示狐狸於二場域間的跨越過程,作者將狐狸的誤聽「Pippilothek」當作一種顯性跨越,即自「Jagdgebiet」過渡「Pippilothek」至「Bibliothek」的循序式變化。場域的改變讓處於劣勢的老鼠理所當然地躍升主導地位,因為牠擁有新場域——圖書館的知識,知識就代表了某種力量。老鼠正式向狐狸宣告:「這裡不是打獵的地方,是圖書館。」(Das ist kein Jagdgebiet, sondern einen Bibliothek.)
這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引出圖畫書欲提供讀者的三大主軸:
(1)圖書館的作用、規範與定義:作者以圖書館的實際作用與規範引出「圖書館」概念。首先,這是一個安靜的特別場域,「怎麼可以這樣大聲吵鬧!」(Hier soll man niemanden stören.)其次,沒有任何東西是屬於特定對象的,「這裡沒有東西會是你的⋯⋯這裡的東西只能用借的」(Dir gehört hier gar nichts…Hier kann man alles nur ausleihen…)。就在此時,老鼠向狐狸宣布了這個新場域之名——圖書館。
「讀⋯⋯什麼啊?」(Was ist eine Pippilothek?)作者緊接著利用狐狸拋出了關於圖書館名稱及定義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從狐狸的用詞可見,牠對於圖書館仍不了解)並引出「書本」概念。文本繼續提到其他圖書館守則,諸如:書本閱讀完後應放回架上、借閱後需保持物品的完整性並歸還、借書證的作用以及單次借書量等等。
(2)書本的種類、功能與用途:文本以三個動詞概括書本對於人類的作用——體驗(erleben)、學習(lernen)以及獲得不同想法(andere Ideen kommen)。想當然爾,老鼠向狐狸展示的第一本書正是圖畫書(Bilderbuch);此外亦提及書本的不同形式——有聲書與一般紙本書;以及書本不同的主題類別——諸如:故事書、食譜、百科全書等等。展示的用意,便是為了引出「閱讀」概念。
(3)閱讀能力的培養:「識字」是閱讀能力培養的一大關鍵,但是狐狸與大部分學齡前的孩子一樣「不識字」,因此作者提出另一種閱讀可能:朗讀(朗讀CD與母雞的朗讀)、傾聽與共讀(與母雞的共讀)。上述三條軸線的開展,使得老鼠與另一隻母雞都得到了生命上的救贖;與此同時,狐狸亦從目不識丁的文盲,開始有了新的閱讀體驗,並有了自閱讀而生的身份變化——從圖書館的入侵者變成借閱者與讀者。
「Pippilothek」一字,無論在書名或內文中都有著重要的一席之地,它展示了一種對於閱讀的「不」知與好奇,因為它正是狐狸復述老鼠口中的「Bibliothek」所產生的新詞,更是一場「圖書館上演的奇蹟」 (eine Bibliothek wirkt Wunder)。除了拼字與發音上的差異之外,「Pippilothek」更是從「不」知進入到圖書館概念的一個重要過渡,簡單地來說,它跨越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場域。
根據安卓.拜米勒(Andrew Biemiller,1906—1982)的研究,年幼的初級讀者在犯錯時,一般會出現三個短暫卻容易預料的步驟。其中當這些初級讀者學習到形素、音素間對應關係的規則後,可能出現的錯誤,多半都是將字形相似、但語意上沒有關聯的字讀錯(註4)。例如將「horse(馬)」讀成 「house(房子)」;或者就是像狐狸那樣——把「Bibliothek」說成了「Pippilothek」。
將狐狸視為初次學習文字閱讀的兒童,在進入文字的第一個口傳聲音中產生誤聽,這在兒童的語言學習中是常見的;不僅如此,狐狸在聽到這個不慎理解的聲音時,便立即將這個新穎的生字與先備語言中感到有趣的字彙結合——「pippi」與「bib」在發音上是對應得上的。文本中的狐狸並未察覺自己竟在無意間創造了一個新詞,牠停留在一知半解的位置上靜靜等待讀者發現,並笑出聲來。
狐狸展示了兒童在面對新字時可能會有的表現,這種錯誤重述不在乎正確與否,反而著重在聲音與趣味性上,它更能使之產生記憶點,幫助正確的單字「Bibliothek」被內化吸收下來或完全被錯誤取代。正體中文譯本將「Pippilothek」譯作「讀」書館,這種譯法呈現安卓.拜米勒研究中,初級讀者最後階段的犯錯模式,即在字音與字意上出現適切性,混淆的二個字之間不單是字音上的類似,字義上也會有所相關。例如將英文「ball(球)」讀成「bat(球棒)」(註5)。由此看來,「讀書館」與「圖書館」的對應關係並無法等同「Pippilothek」之於「Bibliothek」。
正體中文譯本書名省略「Pippilothek」一詞狹帶意涵,直接譯作(或作另命名)為「圖書館」,無法從中看出「Pippilothek」與「Bibliothek」的差異;並將內文中提到的「Pippi」音譯作「讀……」。暗指狐狸將圖書館聽成「讀」書館。此舉卻忽略文本對此一詞語所賦予之意義——這是一個因為誤聽、不明白所產生的新詞。根據Duden字典的解釋,「Bibliothek」由字首「biblio-」與字尾「-thek」組成,分別有「書本、紙張相關」與「集合、聚集」之意,簡單說來,「Bibliothek」即為書本之聚集處。「Pippilothek」係「Bibliothek」一字之變化形,若以上述造字法分析「Pippilothek」一字,那麼這就是一個「pippilo集合或聚集處」。
「pippilo-」並非作者的憑空造字,「pippilo-」正是由瑞典作家林格倫筆下的Pippilotta(長襪皮皮)一角變化而來,Pippilotta恰與文本中的狐狸一樣不識字,指稱了狐狸進入圖書館前對於書本與文字的無知。Pippilotta作為遠離文字閱讀的一種代表,而「Pippilothek」展現的正是從那樣狀態進入文字閱讀之過渡,它既是Pippilotta的聚合,亦是通往「Bibliothek」的過程。
正體中文譯本選擇以「圖」字類音「讀」作為翻譯,試圖營造出「Bibliothek」與「Pippilothek」之間的讀音差異;而在文字意義上,因語言文化差異,正體中文譯本棄絕了「Pippilothek」與「Pippilotta」間的互文關係,僅以「讀」作為一種誤聽,實在無法讓人信服那是一隻對於「圖書館」毫無認知與了解的狐狸。畢竟,圖書館的的確確是供人「讀書」的一個「館」。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指出,「讀」涵蓋了「照著文字念」、「看」以及「研究、專攻」之意(註6),與圖書館所指涉的功能相互呼應。所以當狐狸向老鼠提出「讀⋯⋯什麼啊!」的疑問時,原初的無知就成了一種不安好心。
另外,若以「Pippilothek」與「讀書館」作為狐狸對於圖書館認知的表徵,那麼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二者相較之下在此認知進程中就出現了時間上的極大差異。嚴格說來,此一翻譯選擇已然斷絕文本的後續發展,完全遠離作者的原始設定,畢竟圖書館與讀書館在意義感知上實在太過相近。
源語文本中狐狸問道:「一間Pippi⋯⋯什麼?」(Eine Pippi... was?),「一間圖書館。」(Eine Bibiliothek.)老鼠說。爾後狐狸環顧四周,想要從視覺經驗判別出老鼠說的這個聲音究竟代表什麼意義,卻對此一陌生場域感到全然的未知,因此狐狸繼續問了第二個問題:「什麼是Pippilothek?」反觀正體中文譯本中的狐狸,在環顧圖書館之後,便能以該地域的正確名稱提問:「什麼是圖書館?」也就是說,在環顧圖書館四境後,狐狸已經對圖書館產生了不少概念,畢竟在正體中文的語境中「讀書館」與「圖書館」之間的差異性不大。這也使得老鼠後續對於圖書館作用、規範與定義的解說顯得較為多餘,這正是因為正體中文譯本對「Pippilothek」一詞特性的完全屏除,使得「讀書館」僅成為狐狸的一次性誤聽,而這隻對文字、閱讀、拼音概念一竅不通的狐狸,似乎正運用口傳的力量,證明文字學習的不必要性。如若口傳真能一字(音)無誤,那麼又何必需要保存大量文字紀錄的圖書館呢?
第一次進入圖書館的狐狸,連完整的(錯誤的)「Pippilothek」都無法順利說出。「Eine Pippi ...was? 」是一個「聽」起來好笑的問題。因為「pippi」正好與兒童語「Pipi」同音,是「尿」的意思。兒童對於排泄物等字詞所引發的嘲弄性笑聲,以及疊字疊音產生的可愛趣味性,更是「Pippilothek」的造字巧思。隱晦得令人發笑的「排泄物」與正經八百的「圖書館」或「讀書館」,聽起來是那麼的千差萬別。
翻譯定然使得新創字「Pippilothek」無論在文字意義與聲音意義上均有所流失,只是正體中文的翻譯選擇——「讀書館」一詞,恰恰堵住了所有的可能:無論是與目不識丁的長襪皮皮之間的互文性、諧擬尿尿聲音的隱晦嘲弄笑聲;或是對文本敘事的完整呈現。新創字影響讀者的閱讀樂趣,它們藉由字音、字義或字形展示出來。培利.諾德曼曾以愛德華.李爾(Edward Lear,1812—1888)的無稽詩 〈貓頭鷹與貓咪〉(The Owl and the Pussycat)中的新創字「runctible spoon」為例,討論令讀者感到陌生的新創字,在閱讀上所呈現的趣味可能:
「⋯⋯ 我們若從這個角度思考〈貓頭鷹與貓咪〉,也許可說這首童詩的蘊含對象是喜歡「瓤澀缽」這類怪字的奇特性,又不會因字意不明而惱怒的讀者。文學文本在要求我們具備必要的詮釋技巧,並且了解趣味所在」(註7)
從這段文字看來,培利.諾德曼並不認為兒童會因為奇怪的語言而感到陌生,甚至在閱讀的過程中能感受到對於新創字喜歡及其引發的樂趣。「Pippilothek」一詞在文本中也起了相應的功能;除此之外,正是它奇怪的聲音、特殊的造字與陌生的意義,作用在讀者閱讀的樂趣之上,作為整本圖畫書的引言。既然兒童的包容性比成人假想的還要大得多,翻譯時何不更勇敢地將這些具有聲音特色、隱晦意義及與其他故事互文的新創字,更大膽地以譯語展示出來。
(註1) Amelie Fried(艾蜜麗.弗利德),張莉莉譯,1999,《爺爺有沒有穿西裝?》,臺北:格林文化。
(註2) Linda Ashman(琳達.艾許曼),黃筱茵譯,2017,《誰是小香?》,臺北:小光點。
(註3) Lorenz Pauli(羅倫斯.波利),李紫蓉譯,2013,《狐狸愛上圖書館》,臺北:小天下。
(註4) 參自:Maryanne Wolf(瑪莉安.沃夫),王維芬、楊仕音譯,2009,第171-172頁。
(註5) 同上註。
(註6)「讀」,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mini.moe.edu.tw/cgi-bin/gdic/gsweb.cgi?ccd=1BhcsQ&o=wframe03.htm,下載日期:2018/12/17。
(註7) Perry Nodelman(培利.諾德曼),劉鳳芯譯,2000,《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臺北:天衛文化,第33-34頁。
責任編輯:王予彤、李季芳、黃懿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