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薛巧妮
圖:取自網路
照片:感謝宋珮老師提供
講者:宋珮(圖畫書評論家/藝術研究者)
(編按:本文與斗六繪本館合作,為2023/5/23「2023年繪本翻譯知多少:與繪本譯者有約」系列線上講座紀錄)
當你在網路書店搜尋圖畫書,偶爾會見到宋珮的名字,她寫的導讀使你得以更細膩、深入地品味那本書;當你在搜尋引擎鍵入宋珮的名字,你會發現,她不但身兼圖畫書獎項評審,也在學院和讀書會開設關於美學藝術欣賞、圖畫書敘事分析等課程。
但你知道,宋珮居然也「斜槓」擔任繪本譯者嗎?她介紹自己「喜見圖文以書的形式共同敘事的巧妙豐富」,實際上,不只圖文並茂的精采,她也醉心於語言轉換的字字珠璣。她由衷地說:「圖畫書想翻得好並不容易,我對每個字時常思考良久,有時候光一個字就要想一星期,就以『字字計較』為講題,形容我翻譯圖畫書時的心情。」
宋珮究竟是怎樣開始接觸圖畫書翻譯?回顧這段歷程,她有什麼精華內容想和各位讀者分享?翻譯上又有什麼樣的堅持與風格?

圖畫書翻譯啟蒙書:《愛蜜莉》
追溯圖畫書翻譯的契機,潘人木翻譯的《愛蜜莉》(Emily)是宋珮的啟蒙書。三十多年前,她在國語日報社等待女兒學完芭蕾舞下課,就坐著看書打發時間,沒想到一翻閱《愛蜜莉》,就被深深吸引,被文字傳遞的美麗意境給攫住。
愛蜜莉.狄金生(Emily Dickinson , 1830~1886)是十九世紀美國女詩人,這本書採用第一人稱,由一個小女孩自述她與愛蜜莉相識的經過。譯文寫道:
我們那條街上,有一位阿姨(woman)。人們在背後叫她『神祕女郎』(Myth)。她跟她的妹妹住在我家對面那棟黃色房子裡。她的臥室就是房子正面在左上方那一間,要是你踮著腳走過,就可以看見那間屋子正從高高的樹籬上方偷看你呢。
對照原文,潘人木將「woman」譯為「阿姨」,比起翻成「一位女人或女子」,讓中文讀者感覺親近許多;她再將「Myth」譯為「神祕女郎」,既使用中文讀者熟悉的語言,又不違背本意。值得注意的是,故事雖以孩童的眼光出發,卻是以成人成熟的文字來表達,童稚的心境和語氣在翻譯上如何轉換,又如何取得平衡,也是一門大學問。

而《愛蜜莉》是本關於詩人的圖畫書,許多文字也如詩,潘人木將其詩意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愛蜜莉寫給女孩愛彈鋼琴的母親的信(附上押花):「親愛的芳鄰,我的心就像這些花朵,你的音樂將使它復活,那就是我的春天。」還有以下這一段:
小女孩問爸爸:「什麼是詩?」
爸爸說:「你聽媽媽的琴聲。她這樣一遍又一遍的彈著同一首曲子,有時候會令人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好像那音樂開始有了生命,使你全身震憾。你沒有法子解釋這種力量,真的,它就是一個祕密。當文字也有這種力量的時候,我們就叫它是詩。」
宋珮認為,作家的原文若有這種像詩一般的力量,翻譯時如何繼續保有這種生命力,讓它不致失去,對譯者可說是最大的考驗。
第一本譯作:《爺爺一定有辦法》
三十多年前,宋珮翻譯第一本書──《爺爺一定有辦法》(Something from Nothing)。她很感謝當時編輯的信任,把這本書交到她手中。而編輯是翻譯圖畫書出版的幕後功臣之一,他們會不斷和譯者討論,哪些字句、語氣怎麼翻譯會更好,直到雙方滿意而定稿,再經排版與校對;之所以還需校對文字,是為了檢視圖畫書翻頁或者文圖互相呼應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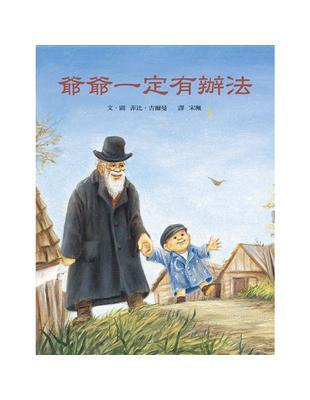
《爺爺一定有辦法》是許多讀者心目中的經典,敘述一位猶太爺爺為了孫子約瑟,將一條毯子變成外套,再變成背心和鈕扣,愛物惜物,流露濃濃的親情。故事開頭寫道:「當約瑟還是娃娃(baby)的時候,爺爺為他縫了一條奇妙(wonderful)的毯子……」「baby」若譯為「嬰兒」,便沒有那麼生動,於是宋珮將它譯為「娃娃」。而有些人認為,「wonderful」在英文裡有時只是綴飾用的形容詞,不需要刻意翻譯出來,但她想了半天,依然把它翻成「奇妙的」,因為作者菲比.吉爾曼(Phoebe Gilman)形容這條毯子「又舒服、又保暖,還可以把惡夢通通趕跑」(to keep him warm and cozy and to chase away bad dreams),它不像一般的毯子僅僅舒服保暖,還能趕走惡夢,很奇妙吧!後來,毯子變成了外套,外套舊了,又變成了背心,還可以變成領帶……最後竟然變成了一顆小鈕扣,在爺爺神奇改造的過程中,宋珮一律將「wonderful」譯為「奇妙」,藉由重複的字句形成節奏感(上述譯文「又舒服、又保暖」同理)。
這些東西變得又破又舊後,約瑟捨不得丟,總會胸有成竹地說:「爺爺一定有辦法!」(Grandpa can fix it.)原文直譯是「爺爺能修理(改)」,但宋珮認為這簡單的一句話承載著小男孩對爺爺堅定的信心,必須將約瑟深信爺爺無所不能的意涵翻出來;在編輯的建議下,「爺爺一定有辦法」也成為這本書的中文書名。
《爺爺一定有辦法》全書字句充滿韻律和動感,比如:「『嗯……』爺爺拿起剪刀開始喀吱、喀吱的剪,再用針飛快的縫進、縫出、縫進、縫出。」(”Hmm,” he said as his scissors went snip, snip, snip and his needle flew in and out and in and out.)原文裡,剪刀「snip, snip, snip」,針則「flew in and out and in and out」,為將重複字句的節奏表現出來,宋珮增加了擬聲字「喀吱、喀吱」;和編輯討論後,也以「縫進/縫出」兩字取代「縫進去/縫出來」三字,藉此表現速度。
詩意、人稱、語氣
翻完《爺爺一定有辦法》,宋珮發現自己不僅喜歡翻譯有節奏的文句,也相對擅長。她認為每名譯者都曉得自己適合翻譯什麼樣的文字和語氣,以針對每本書的特色去翻譯,因此近年譯作越來越少,通常只翻譯自認能夠表現出原文意境和感覺的作品。
宋珮對詩意的文字情有獨鍾,雖然極具挑戰性,但也樂在其中,像是《如果你想看鯨魚》(If You Want to See a Whale),這本書也有許多重複字句,一開始就帶給讀者「懸念」:
如果你想看鯨魚
你會需要一扇窗
還需要一片海洋
還需要時間等待
還需要時間觀看
還需要時間猜想「那是不是鯨魚?」
if you want to see a whale
you will need a window
and an ocean
and time for waiting
and time for looking
and time for wondering “is that a whale?”
宋珮分享,英文裡的「A」(一)有時未必需要翻出來,免得讀起來冗贅、繁複;至於將「and」譯為「還」而不是「和」,是為了保留原文「等待鯨魚出現」意猶未盡的綿長意味。還有一段譯文讓她特別下工夫:「當你在等待鯨魚的時候/或許會有海盜/但他們幫不了忙」(because possible pirates won’t help at all when you’re waiting for a whale)作者茱莉.福萊諾(Julie Fogliano)刻意使用「possible pirates」,押頭韻(p),她翻譯時便也依樣畫葫蘆,不用「也許」,而是以「或(ㄏ)許」呼應「海(ㄏ)盜」。
翻譯詩意文字,需注意節奏、押韻和字數(會影響節奏),譯者會設法貼近原文,有時卻難免力有未逮。此外,翻譯還需考量「人稱」和「語氣」,宋珮繼續以譯作為例說明:《寶兒:穿背心的野鴨》(Borka: The Adventures of a Goose With No Feathers)採用「一本正經的全知觀點」,描述野鴨家族的歷史,她便以說故事的語氣翻譯:「從前,有一對野鴨夫婦,他們是波朗先生和夫人」(Once upon a time there where two geese called Mr. and Mrs. Plumpster.),譯文維持「娓娓道來」的敘述風格。
有些作品雖採用全知觀點,但夾雜作者的評論,向讀者表達自己的看法或是替角色發言,比如《藏起來的房子》(The Hidden House):「有時候,布魯諾會和他們說話,但是說的不多,因為布魯諾很清楚,他們是木頭娃娃,不能回答他。木頭娃娃雖然不說話,但是我猜他們很快樂。」(Bruno talked to them sometimes, but not very much. They were wooden dolls and they couldn’t talk back, and Bruno wasn’t stupid. The dolls didn’t talk, but I think they were happy.)這段話中,作者馬丁.韋德爾(Martin Waddell)自己跳出來說話了。而宋珮將「think」譯為「猜」,認為比譯為「想」更有力,更能表現作者介入的意識。
《兩隻壞螞蟻》(Two Bad Ants)表現的是有限制的第三人稱觀點,採取角色(小螞蟻)看待事物的角度:「消息在螞蟻王國的坑道裡傳得很快,一隻偵查蟻帶著了不起的新發現回來──一顆美麗耀眼的水晶(cystal)。偵查蟻把水晶獻給蟻后,蟻后嘗了一口,立刻把整顆水晶吃了個精光。」螞蟻眼中的「水晶」,其實就是人類所說的「糖」,文字既是全知的觀點,也是螞蟻的視角。
《隨光轉動:亨利.馬諦斯的虹彩之舞》(The Iridescence of Birds)描述的是大畫家馬諦斯(Henri Matisse)的故事,採取第二人稱觀點,是一種與讀者互動的語氣:「假如你是個叫做『亨利.馬諦斯』的男孩,住在法國北部的沉悶小鎮,/那裡的天空總是灰濛濛,天氣冷颼颼。/你渴望色彩和光線,也渴望太陽」(If you were a boy named Henri Matisse who lived in a dreary town in northern France where the skies were gray / And the days were cold / And you wanted color and light / And sun),敘述剛開始就假定讀者是馬諦斯本人,並一步步引領讀者進入他的生命。
《城市裡的小訪客》(Small in the City)採取第一人稱觀點,描述小男孩穿越大街小巷,想要幫助一位特別的朋友,文字透露男孩主觀的情緒,圖畫則客觀地表現故事場景和情境:「我知道,在城市裡會感覺自己很渺小。/沒有人注意你,喧嘩聲大到令人害怕,有時候,你真不知道該怎麼辦。」(I know what’s like to be small in the city. / People don’t see you and loud sounds can scare you, and knowing what to do is hard sometimes.)這段話中的「你」,既像小男孩對讀者說話,也像他在心中喃喃自語。






特殊文體:祈願詩、頌歌
除了上述簡介的人稱和語氣,宋珮也譯過「祈願詩」這類特殊文體,它伴隨著敘述者的祈求。《天亮之前》(Before Morning)描述深沉的冬夜裡,小女孩不忍心飛行員媽媽得出門工作,便祈願上蒼下一場大雪,讓雪花阻止媽媽離去的腳步,將媽媽送回她身邊:「求祢興起漫天雪花,/懇求祢,就這麼一次──在天亮之前改變世界」(let the sky fill with flurry and flight / Please-just this once-change the world before morning)原文中並沒有「you」,但女孩祈求的對象是掌管天氣的神,中文便需譯出來。
另一種特殊文體還有「頌歌」,比如《太陽弟兄,月亮姊妹》(Brother Sun, Sister Moon)。本書原為亞西西的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寫的讚美詩,詩歌裡描寫他在義大利鄉間的美妙感受,用的是家鄉翁布里亞淺白的方言,再由凱瑟琳.派特森(Katherine Paterson)想像這首歌的意境,用詩的語言加以改寫:「天地的創造主,祢用無上的能力與慈愛創造了萬物,看一切為美好,我們要唱一首歌讚美祢。」(We comes to sing a song of praise to you. O God. The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宋珮調整語句結構,將讚美的對象(神)提到句子前面;她也將文本提及的擬人化自然現象,譯為「弟兄」(Brother)而非「兄弟」,在基督信仰裡,人們便是以此相稱。這本圖畫書出版以前,宋珮有許多機會將譯文念給許多人聽,朗讀幫助她刪掉多餘的字眼,也讓文意表達得更明白,更能掌握字句的節奏。「要一直唸一直唸,直到文字生出生命力,讓它們可以直抵人的內心裡,才算是好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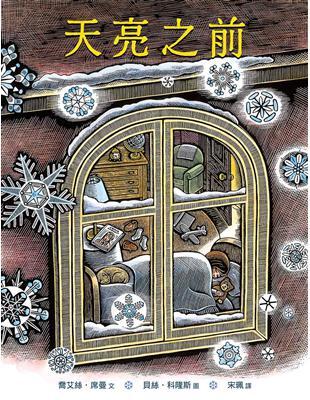

回顧翻譯圖畫書的歷程,宋珮對譯文的堅持與要求,誠如她所說的「字字計較」,這麼做的背後或許能以一句話貫穿──她相信文字充滿力量,而好的文字自有生命。於是,讀者們有福了,因有她美好的譯文相伴。
講者簡介|宋珮
加州大學(U.C.S.B)藝術史碩士。1990年代開始對圖畫書的圖像敘事產生興趣,繼而從事圖畫書翻譯、評論、導賞、評審等工作。至今翻譯圖畫書一百餘本。
繪本譯作|《雨果的祕密》、《爺爺一定有辦法》、《畫了一匹藍馬的畫家》、《阿姆,謝謝你!》等作品。
責任編輯:張惠鈞、曾邢家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