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曹一竹
圖:由本文作者提供
撰文時間:2020年6月
影片簡介
紀錄片《說Ina的話》採訪了在花蓮太巴塱、港口部落以阿美語從事創作和族語推廣的三個團體——分別是以阿美語創作歌謠及唸謠、製作多部音樂動畫,讓孩子在生活中學習母語的「Tamorak阿美族語共學園」;把各族群神話融入行為藝術表演、在訓練過程之中傳遞部落精神的「Langasan Theatre冉而山劇場」;以及從用阿美語說故事給孩子聽,到自己開始創作出版阿美語繪本的「Liso^so’你說說工作室」。
正片觀賞 (請點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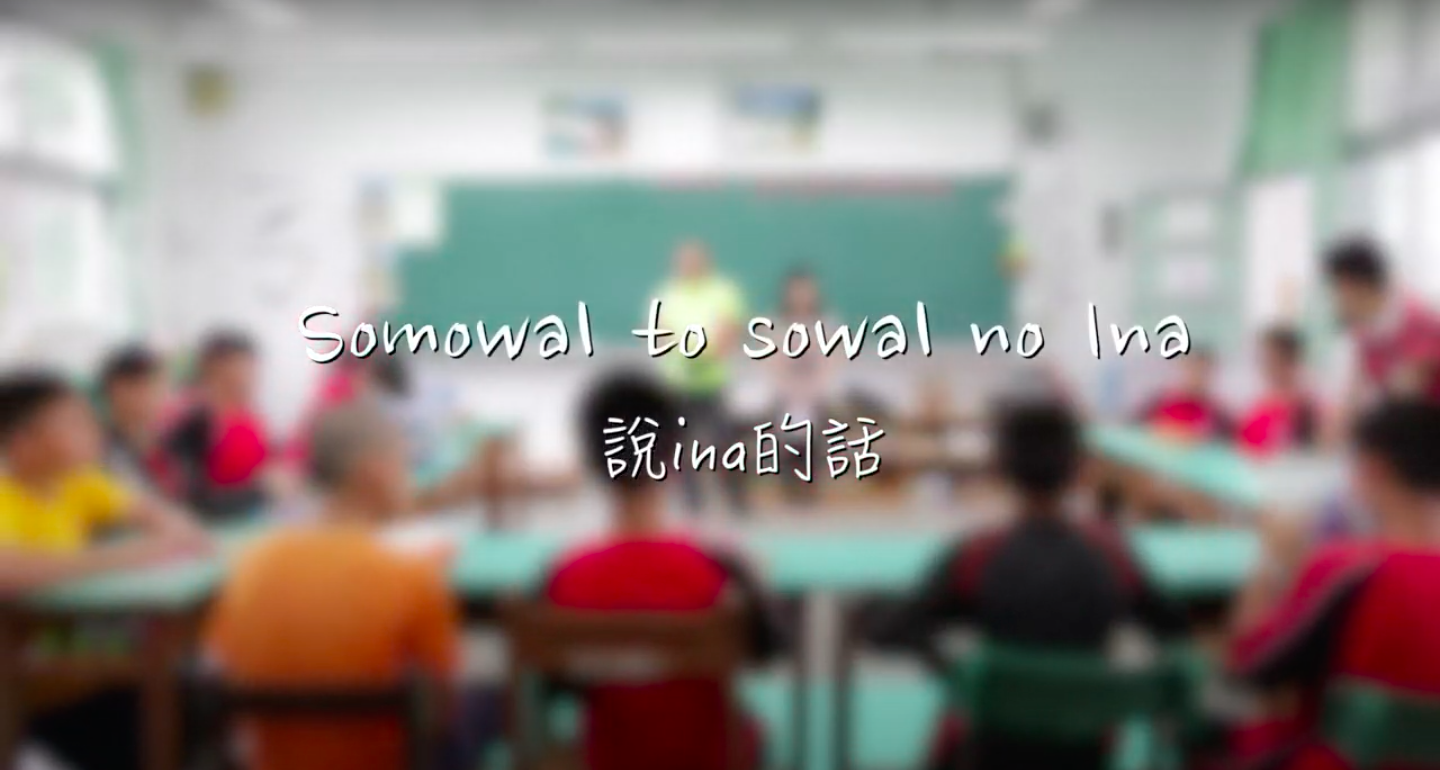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4YZUfgG6eM
拍攝緣起
拍攝紀錄片的想法源自於對這對夫婦的好奇——Moli Kati(摩力.旮禾地)和Awa(劉于仙)。阿美族出身的Moli是冉而山劇場的歌手,也是一位畫家和阿美語的翻譯,年輕時因為事故失去了一條腿,卻在回到部落理髮店為老人們理髮的過程中,重新認識了自己生長的部落;Awa原是一個留學法國學習戲劇的漢人女孩,如今一開口能熟練地吟唱阿美語的歌謠,講起部落的事情興奮得像個小孩。這對夫妻檔不僅到各地用阿美語為孩子講述繪本故事,也嘗試創作與阿美族生活相關的繪本。
臺灣雖為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但在將近一百年的禁說方言政策與國際化的浪潮影響之下,各族的原住民幾乎都面臨著語言與文化逐漸消失的困境,但這一對夫婦,在講到這個通常帶著嚴肅與悲傷的議題時,我在他們眼中看到的,不是無可奈何的無力感,而是樂觀、活力與挑戰。我看得出來,所謂的「文化意識」在他們身上是很高的,即使他們來自不同的族群,代表著不同的年齡層,觀念上卻相當一致。
他們的積極,漸漸聚集了一些來自各地,與他們相同理念的人。這讓我開始好奇,這群年齡主要介於30~40歲、來自不同族群的人,他們會怎麼做,去改變文化消逝的現況,留給孩子他們認為最珍貴的部落價值?
說Ina的話
「Ina」在阿美語裡是母親的意思,在影片的開頭,我寫下了一段話:「在花蓮有一群人,用他們的方法,試著讓下一代,不要忘記母親的話。」我想這是此次採訪到的每個人共同的心願,母親指的不僅僅是生出自己的人,也是指孕育這整個民族世世代代的祖先。
Awa夫婦於2018年創立了「Liso^so’你說說工作室」,阿美語Liso^so’的意思是陶壺上有了裂縫,水從這個裂縫中持續不斷的滴落,源源不絕的樣子。為了不讓族語隨著時間消逝,一開始他們透過一個月一次紀錄部落耆老的對談與吟唱,保存阿美語的詞彙與用法,他們說,上一代的用語有時候相當的詩意,記得有一次,一位耆老自我介紹的第一句話就說:「我是一個膝蓋長滿青苔的老人。」Moli現場翻譯給Awa聽的時候,Awa愣住了,不確定是什麼意思,Moli才補充道:「我想他是想表達他真的很老很老了。」這句話讓Awa記憶深刻,後來這句話也成為了Awa繪本創作中的文句。
順著Awa夫婦這條線,我陸續認識了和他們合作創作的繪本小組成員、引領並加深他們對於部落文化認同的重要推手——冉而山劇場的創辦人Adaw Palaf Langasan(阿道.巴辣夫.冉而山),以及身為漢人,卻打造了Tamorak阿美族語共學園,以沈浸式教育教授部落孩子族語的Nakaw (林淑照)老師。這群擁有著無比勇氣和毅力的開創者們,成為了我這次紀錄片主要拍攝的對象。
歌謠中的歷史
「以前沒有文字的時候,只有語言,我們是靠著歌謠這樣一代一代傳承的。」冉而山劇場的團長,同時也是太巴塱部落長者的Adaw這麼對我說。他說,他的個性漂泊不定,一生跟過許多劇團,記得有一次跟著一個劇團做田調去到一個深山的部落,部落的人帶了一大盆酒,邀請他們喝完後一人吟唱一曲,等大家都唱完後便輪到他們部落的人唱,他們一直唱一直唱⋯⋯夜深了,Adaw在迷濛之中睡著。等他再睜開眼,天已初白,而這群人依舊還在唱著歌,Adaw很驚訝,便問同行的團員,他們究竟在唱什麼?「原來他們唱的是老祖先的歌、遷徙的歌、神話傳說的歌,一曲接著一曲,永遠唱不完。」
原住民因為沒有文字,一直都是以口傳文化傳承著集體記憶,其中歌謠的重要性就如同史書一般,記載著各民族的起源。Adaw研究各個民族的神話傳說故事,分析裡面的情節和元素,把它應用到劇團的表演中,他說:「現在的部落雖然很零散,但是只要還懂得神話傳說故事,就能夠找到一個根。」他對傳承的盼望,傳遞到了曾參加劇團研習營或演出的學員們身上,Awa與Moli便是從Adaw身上,學習到了對自然及先祖的誠懇、敬畏與謙卑的態度,並且透過另一種藝術形式,希望再繼續把這個精神傳承下去。

圖1 Langasan Theatre冉而山劇場創辦人Adaw研究各民族的神話傳說及歌謠,將其融入表演之中。
從口傳文化進入到書面文化
在劉秀美所寫的<臺灣原住民族口傳文學的想像與真實>文章中曾有過這麼一段敘述「很早以前,我們和漢人一樣是有文字的。漢人把文字寫在紙上裝進瓶子裡,我們認為那樣不容易保存,便把文字刻在石頭上。後來洪水來了,石頭和瓶子都被水沖走,我們的文字隨著石頭沉沒而消失了,漢人的文字則因為瓶子漂在水面上而保存下來。」原住民語言沒有文字的這個特性,使得以往的原民創作著重在口傳文化上。然而在現代,原住民的文字已經能用羅馬拼音來表示,創作的面向和方式又更加多元,而圖文並置的繪本創作,也是進入書面文化階段的一個象徵。創作的主題也從以往的神話傳說故事,漸漸演變到一些與生活相關的原創故事或是知識性的繪本。
族語創作的挑戰
儘管原住民繪本大部分還是承載著教育的目的性,但是呈現的方法越來越多樣化,「Liso^so’你說說工作室」的繪本小組成員,也積極的參與工作坊與演講,試著去了解圖文關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然而最大的困難,還是要以阿美語的語言邏輯來書寫文字這件事,因為耆老們族語能力好,但沒有學過拼音,也鮮少能做繪本的創作;年輕的一代能夠吸收新知,有創意,卻很少有能力去書寫族語。因此在寫故事的時候,需要族語翻譯的協助,但是以中文的邏輯來書寫故事的話,阿美語語言中的趣味和其特有的思考方式,便很難展現出來。
比如Awa與Moli合作創作的一本以開鑿蘇花公路為主題的繪本《Talacowa Kamo循山》,其故事內容是從一首歌謠去改編的,這首歌共有12段,寫出了一個被日本人領班強迫去作苦役時,一位阿美族人思念家鄉的心情。歌曲的最後一段寫道:
Ororay a to^od (勞累 身心)
Patadas sa a orip (以前一開始的生活很勞累)
Anini han o rihadayay(現在的生活是安適的)
To ko saka o mamis, (這條路往北邊)
Hay ira ayaw to rakat(以前都是用走路的)
To rakat no paliding (現在都是車子在走路了)
他們提供翻譯文稿中,第一句話是還沒有轉成中文邏輯的阿美語直翻,從這裡可以知道阿美語習慣把主詞放在句尾,與中文的語序是相反的,這樣的語法在繪本中設計的斷句點,以及押韻都會和中文有所不同。而最後一句話「現在都是車子在走路了」則在語言中表現了時代性,以及都市人和原住民看待交通工具角度的差別,都市人常說「以車代步」,而原住民卻說「車子走路」,這便是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語言趣味性。
要克服這個問題,還是得回到族語的教育上,我認為年輕的一代若能夠靈活的運用族語,以阿美語的語言邏輯來思考,才能真正創作出具有阿美語特色的文學、繪本創作。

圖2 Liso^so’你說說工作室創辦人Awa與Moli夫婦不只以阿美語說繪本故事,也從事族語繪本的創作。
心之所向,即為故鄉
深入拍攝之後沒有多久,便發現在母語推廣的實踐中,因通婚而嫁入阿美族的外地媳婦們發揮了強大的力量,她們其中有許多是漢人,投入的程度卻不亞於自己的另一半。
Tamorak阿美族語共學園的創辦人Nakaw即是很好的例子。她在1998年因為認識了港口部落的頭目而來到這裡教書,頭目當時已經高齡90歲,待她如自己的孩子,Nakaw也視頭目為自己的另一個父親。老頭目過世之前,要Nakaw去想想三個問題:第一,為什麼現在的孩子越來越無法說阿美族語?第二,通婚嫁給漢人的阿美族女性,他們的下一代為什麼好像就不是阿美族人了?第三,在這個國際化的世界,不只有原住民,還有漢人、客家人、日本人、美國人……在這樣的世界中,阿美族的定位是什麼?這三個問題深深地種在了Nakaw的心裡,一直到她後來真的嫁進了港口部落,也生了小孩,她決定信守與頭目的承諾,要讓自己的孩子會說阿美語,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可以往哪裡去。
這條路漫長而艱辛,那時Nakaw自己在港口國小教書,她認為體制內的學校缺乏對部落文化的傳承,有許多地方使不上力,於是她索性辭職,在自己的住所建立起族語共學園,引進華德福的教育方式,用歌謠和生活體驗去教育孩子。但即便她已經嫁進來二十餘年,深入阿美語教育,甚至還能用族語創作,她的漢人身份卻讓她備受質疑——一個漢人能夠真正理解阿美族的部落精神嗎?漢人教的阿美語是正確的嗎?這些問題的答案,Nakaw用二十年來不斷的學習、修正與實踐來回答。她也知道自己教授的阿美語不會有母語使用者道地,但她會去找耆老們請教錄音,探究一個同樣的單字在不同部落間的變異性以及源由;她能單純地欣賞這個語言的美,繁複的探尋過程對她而言不覺得苦,反而樂此不疲。
認同Nakaw的理念而帶著孩子一起來共學園學習的家長中,有歌手以莉.高露和她同是音樂人的丈夫陳冠宇,也有《太陽的孩子》的導演勒嘎.舒米與他的插畫家妻子黃海蒂2,這些家長不僅參與教材的討論,也號召藝術家一起將Nakaw創作的歌謠創作成動畫,成為網路平台上可以共享的阿美語教材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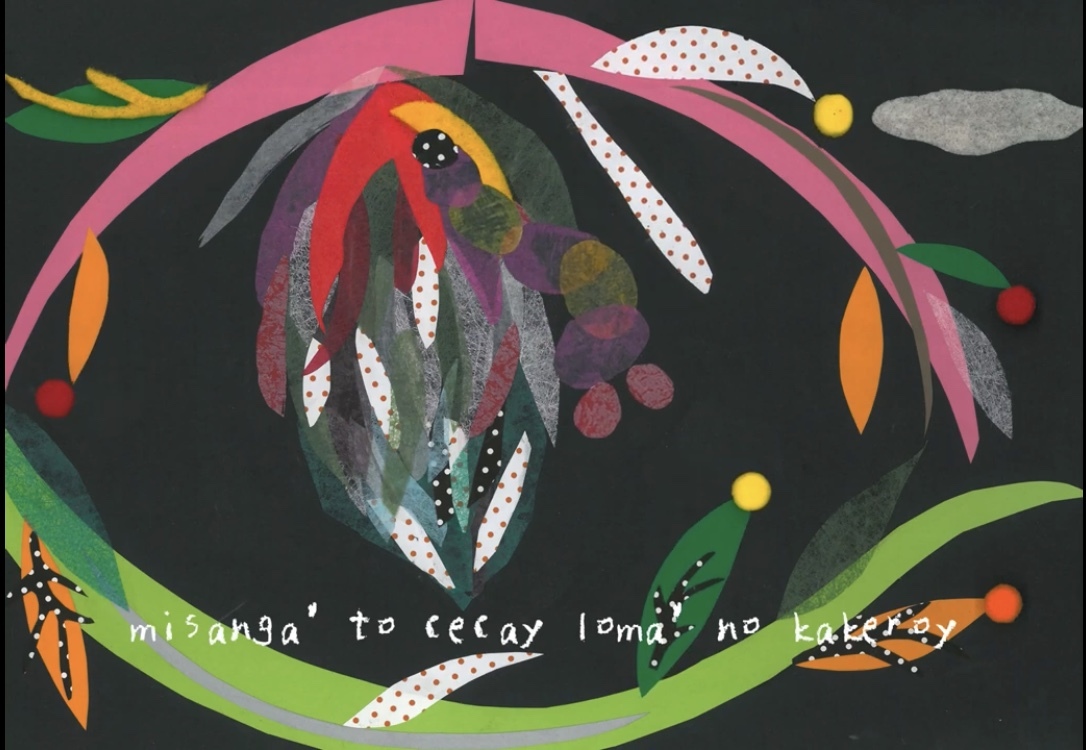
圖3 Tamorak阿美族語共學園的創辦人Nakaw林淑照老師,以阿美語創作歌謠及唸謠,並做成動畫在網路平台上共享教材。
總有一天,在山上碰頭
不同民族的加入,帶來了新的刺激,各自不同的生長背景,也令這些原漢結合的伴侶,可以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彼此的母文化。對於通婚,有些人覺得這是造成語言流失的重要因素,但是在Awa和Nakaw的例子中,卻有了相反的結果。她們之間有個共同點,就是在婚前都遇到了一位給予他們極大感動與包容的部落長者,對Awa而言那個人是冉而山的團長Adaw,對Nakaw而言則是港口部落的老頭目。
紀錄片完成之後,我將影片傳給所有被採訪者,感謝他們讓我有機會學習到這一切。採訪過程中提供我最多協助的Awa回饋說,以前自己在做的時候,遇到很多困難,也常常懷疑自己這樣做是否真的有用?但透過這支紀錄片,她意識到這件事並不是只有她一個人在做,大家都在這條路上一起前進,看見別人也跟自己做著相同的事,是很大的鼓勵。
她的回饋讓我覺得做這次的紀錄片是值得的,我想,世界上還有許多沒有被知道,但默默努力傳承著自己民族文化的人們,大家像是在爬一座很高的山,所有的人都從不同的路上山,他們看不到彼此,所以感到孤獨,但是只要一直堅持地走下去,總有一天,大家會在山頂上碰頭。
< 感謝 >
這部紀錄片從籌劃到完成,集結了許多人的幫助。就讀博士班的陳美齡學姊,長期研究與原住民相關的議題,她的家族故事和對於文化流失的憂心,牽引我對於這個議題產生更加深刻的共鳴,在前期籌劃上我們有許多的討論;擔綱主要攝影師的陳有德是我的先生,他背著攝影和錄音的設備陪著我探訪各個部落,因為有他的協助,我也才能專心投入在訪談上;最後不得不提的是Awa劉于仙,她雖然也是受訪者之一,但其實幾乎所有其他在部落的受訪者,都是經由她的介紹及牽線才得以促成拍攝,她的積極與投入,也不斷地感動著我。謝謝,每一個在這條路上一起努力的人。
1《原住民族文獻》電子期刊第五期,劉秀美,<臺灣原住民族口傳文學的想像與真實>,2012 年 10 月,原住民委員會發行 https://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11&id=677
2以莉.高露、陳冠宇、勒嘎.舒米與黃海蒂的專訪於《曙光》季刊第六期中有詳細刊載,2020年6月,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發行
3動畫教材可於台灣Tamorak文教協會(阿美族語共學園)網站中觀看https://www.tamorak.com/
責任編輯:王予彤、李季芳、黃懿蓉